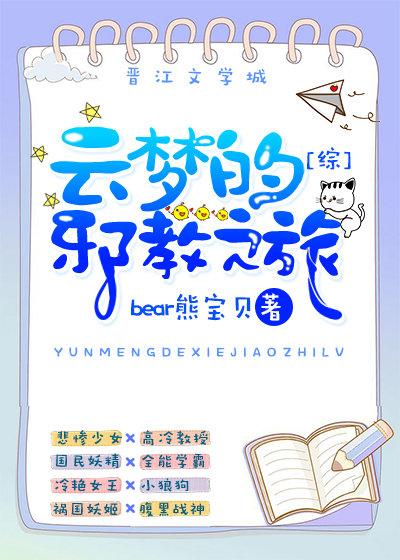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寒门首辅贵女妻 > 第578章 祖制陋习(第1页)
第578章 祖制陋习(第1页)
没有外力所激,皇帝连最后的回光返照都没有,双目无神几近涣散,口不能言,唯独耳朵还能听见些许外界的声响。“曾和郡主闲聊,说人之将死,最后的感知便是耳力。”屋内一个人也没留,只剩下惠嫔和皇帝独处,惠嫔抬眸,眼中哪有一丝悲切,有的只是淡然和冷漠。“这么多年,臣妾还未和陛下好好说过心里话呢。”岁月不饶人,惠嫔气度雅静但姿容到底染上了光阴的痕迹,眼角也有了些许纹路。平日她总带着淡淡的笑意,便是不复青春美貌,也总让皇帝观之可亲,如今笑容淡去,才发现,她的面貌并非似水般柔情,若如娴贵妃一般盛装打扮,定然有不逊色于她的明艳。若非她生得貌美,当初皇后也不会将她送上龙床,想要让她分去娴贵妃的宠爱。对外,皇后母仪天下,端庄持重,可身在后宫,万般不由己,还不是只能像寻常后宅妇人一般,利用婢女的美色争宠。哪怕她知道,惠嫔志不在后宫,只盼着年满二十五放出宫过自在的日子,也依旧选择将惠嫔推向醉酒的皇帝,再关上房门。门内惠嫔的求救和哭嚎,皇后充耳不闻,她从小便是被当做主母教养,怎会将下人当一回事,在她眼中,不过都是些和衣裳首饰一般玩弄鼓掌之间的玩物罢了。惠嫔伸手替皇帝拨开汗湿的发丝,话似寻常般,说着宫中几乎无人知晓的秘辛。“当初您借我的手,给皇后娘娘送的一碗碗藏毒的汤,其实臣妾都知道。”皇帝便是能听见,也难以有丝毫的回应了,惠嫔也不介意沉默的听众,提起旧主的病逝,甚至有些欢喜。“世人皆道您和皇后娘娘伉俪情深,就连皇后娘娘自己也信以为真,却不知最是无情帝王家。您呀,早忌惮她和她身后的宇文家。”当年,皇帝酒后临幸皇后的贴身宫女,皇后大度出面,亲自给宫女求了一个名分。皇帝似乎对那宫女颇为喜爱,短短数月就将她从一个小宫女升为了贵人,在后宫中,惠贵人的风头一时无二。只有惠贵人自己知晓,皇帝对她,或许有几分肤浅的兴趣,但归根结底,是看中了她和皇后的关系。皇后自以为惠贵人成为妃嫔后会对自己感恩戴德,见她每日送来羹汤,也只当她是孝敬。却不知,这些汤都出自皇帝之手,名义是让惠贵人不要忘了旧主的恩情,才好在后宫立足,实则,是钝刀子割肉。皇后病逝后,皇帝对惠贵人也失去了兴趣。惠贵人亲手毒杀了害了自己一生的皇后,却没忘了,那夜将自己压在身下,为所欲为的皇帝亦是从犯。恰在这时,她有了身孕惠贵人知道娴贵妃善妒,若知她有身孕,只怕不会轻易放过她,腹中的孩儿更难以诞生。她先是改变的平日的穿衣打扮,越发素净,不去分娴贵妃的风头,后来,又寻上了在皇帝身边做内侍,和自己同乡的德贵相助。万般小心,忍辱负重,到底让她从娴贵妃的手下求得了一线生机,生下了四皇子,也因此得封嫔位。都说母凭子贵,有了皇子傍身,惠嫔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非但没有靠着皇子争宠,反其道而行之,甚至有意让皇帝对姜询漠视。后来,有些宠爱在身,生下了三皇子的妃嫔便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三皇子的母妃望子成龙,在三皇子才会开口说话,就变着法地教儿子讨皇帝的欢心。一时的春风得意,换来的却是皇子夭折,母妃疯病被打入冷宫的凄惨下场。在惠嫔小心翼翼地护佑下,四皇子姜询虽不顺遂但也算平安长大。知子莫若母,惠嫔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一颗不屈居人下之心,她对此没有半点惶恐,而是十分满意。但当姜询从青州求学归来,带着稍显莽撞的锐利之气时,惠嫔却要求他,去求太子,准允他的追随。“我不!母妃,太子他根本就看不上我!这边算了,他对您还——”姜询自幼被二皇子欺辱,太子虽然没有对他太过打压,但眼中的轻蔑姜询看得清清楚楚。在他的两位兄长心中,自己只是宫女所生的贱种,和他们这些母族高贵的皇子不可相提并论。“询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惠嫔伸手擦去儿子眼角愤慨和委屈的泪花,年复一年的卧薪尝胆,让她的心已沉静如古井。“母妃知道你的委屈,但了解仇人,才是杀死仇人的第一步。”昔年景象如走马灯一般在眼前闪过,惠嫔叹息一声,却没有惋惜之意。她缓缓起身,站在榻前,朝着皇帝深深一拜。“臣妾还得多谢陛下,让臣妾明白,只有站得更高,才能将曾经眼高于顶之人踩在脚下。”“陛下的传位诏书,已经拟好盖印了。只怕臣妾来不及成为您的贵妃,便要成为这澧朝的太后了。”皇帝的指尖似乎颤抖起来,又似乎只是幻觉,只听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不过片刻,又回归沉寂。半晌,惠嫔才起身起查验皇帝的生死,确认他已经没了气息,才伸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合上。她低下头,在皇帝的耳边轻语最后一言。“陛下当年给臣妾的汤,如今自己也尝到了。”殿外,姜询挺直了脊背,跪在中央,其余人自然不能站在一旁,乌泱泱一大片,跟着跪在了后面。忽然,殿门被人从里面吱呀一声打开,惠嫔红着眼眶走了出来,颤抖着半晌才出声。“陛下,驾崩——”片刻的寂静后,便是一片哭嚎,除了在御前当差的侍卫和宫人,还有闻讯赶来的后宫众人。若膝下有一儿半女的妃嫔,哭得便轻松些,靠着子嗣,便是封不了太妃,也可被孩子接到府上供养晚年。那些没有子嗣的妃嫔,哭的才是肝肠寸断,其中不乏年岁青葱,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的年轻女子。按照旧例,没有子嗣的妃嫔,只能给先帝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