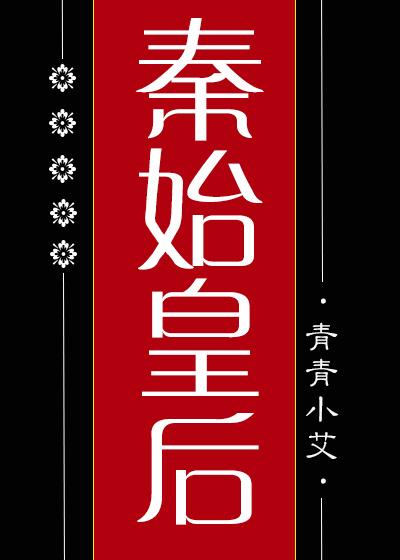墨澜小说>鬼使神差 > 第九章 围堵(第2页)
第九章 围堵(第2页)
连打带踹将那人按进了后座。戴绮思跃上驾驶座飞快地朝反方向驶去。这场逃亡来得突然,一时间我脑子里尚未形成可行的计划。戴绮思也是病急乱投医,小卡车在树林中飞驰,哪里有路就往哪里开,根本不考虑该逃到什么地方去。
我有些恼怒,一把掀开那人的牛仔帽,帽子下面是一张亚洲男子的脸,年纪在五十岁上下,面容坚毅,两鬓带有银丝。见我在瞪他,他立刻反瞪了回来。我记忆里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他莫名其妙的敌意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认识他?”戴绮思从后车镜里瞄了几眼,继续专心开车。
我也好奇,索性将枪口移开,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问他:“咱们没什么过节,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他不吭声,视线不停地在我和戴绮思之间切换,不知道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卡车在树林里颠簸徘徊,时不时与周围的树木发生摩擦,路况非常坏。那人毕竟上了年纪,连番颠簸之下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心说刚才玩匕首的时候不是挺神气的吗,怎么现在开始晕车了。
他双手紧紧地扣住车门上的扶手,不一会儿,额头上渗出黄豆大小的汗珠,瞧这模样应该不止晕车那么简单。我翻开车厢里的储物盒,找出半瓶矿泉水,看看日期好像没什么问题,便揪起他的脖子,一股脑地灌了下去。
“咳咳咳,”凉水下肚,他的精神稍微好转了一些,靠在椅背上,指着我和戴绮思问:“你们,谁是家的人?”
“你想找谁?”我挺起胸膛本能地挡住了他扫向戴绮思的目光。车子忽
然颠了一下,我差点从椅座上滚出去。戴绮思回头道:“熄火了,没油。”
我骂了一声娘,推开车门看了看四周,到处都是树,绿油油的一片,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杂乱的树林里除了我们三人的呼吸之外,不断地有脚步声传来,嘈杂的喊叫离我们越来越近。那群人并没有放弃搜索,而是追着我们一路狂奔而来。树林顶端升起的浓烟昭示着家老宅凄惨的下场。戴绮思甩开车门,将那个男人拽了出来。她的情绪十分激动,这个时候估计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劝不住她。
“走,步行。”她沉着脸推着那个白鬓男子在树林里急行。我问她能不能分辨出路,戴绮思为难道:“隔的时间太长了,只能找到大概位置。他们都是当地居民。我们在树林里没有优势,得尽快找到出路,最好能找到来时的公路。”
想在茫茫的树海中找到来时的路,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别提绕回公路上去。况且我们还带着一个大麻烦。我一度怀疑他就是镇民口中的凶手,昼伏夜出,躲在废弃的宅里掩人耳目。但只要仔细一想就会明白,这个推测太不靠谱儿了。首先我们进屋的时候已经彻底查看过,除了门口的
破锁,并没有任何人侵入的迹象;其次就冲镇上居民放火烧屋那股操行,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躲在房子里,他们还不早就抄家伙把家给拆了,也不必见了我俩的面之后才发作。我推测,他们只是怀疑屋子里藏了人,甚至可能做过排查,苦于无所收获,只好暂时修网通电把家老宅给隔离了。所以当我和戴绮思忽然出现在镇上的时候,他们才会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一个困扰尤塔镇居民多日的谜团即将揭开,怎么能叫他们不亢奋。想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考虑起另外一件事:镇上到底出了什么大事,以至于大家草木皆兵,连执法人员都跟着乱了手脚?
“老哥,你是什么时候到镇上的?”
那人没想到我的态度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尴尬道:“有段日子了。”
“哦,我们刚到,回来祭祖。听你的口音不像华裔啊,大陆人?”
他先是“嗯”了一声,随即警觉地闭上了嘴,大步跟上戴绮思的脚步,不再搭我的话。我走在队伍的尾巴上,边戒备周围的情况,边观察这个白鬓男子。他走路时跛着脚,但身形挺拔没有一丝病态,看样子不像受
了新伤,腿部可能早就有了残疾。他在车上的时候询问我俩身份,说明此人目的明确,早就知道那栋废宅是家人所有。他不远万里从大陆来到美国,为什么要找上家?戴绮思与他素不相识,剩下的两位早已仙逝。单从年龄判断,他与教授是旧识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真是登门寻友,为什么在阁楼上的时候连话都不说一句就忽然向我痛下杀手?回忆起他那副狠毒的表情,我不禁在心中写下了一个沉重的问号,并决定在问题查清楚之前,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戴绮思就是家后人。
戴绮思凭借自己幼时的记忆,带着我们在树林里穿梭,为了避免被追击的镇民围堵,我不时地翻上树端眺望四周的情况。谢天谢地,追在我们后面的都是些普通百姓,如此稀疏单薄的障木林,换几个稍微有点经验的猎人就足够把我们围死了。
“已经甩开一段距离了,保持这个速度下去,他们很快就会放弃。”我跳下树将情况描述给戴绮思听,她的脸色稍稍好转了一些,倒是那个中年男人一直左顾右盼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喝住他说:“事情不交代清楚,你哪儿都别想去!”
他呵呵一笑:“小兄弟,以前当兵的吧?”
“哪儿那么多废话。顾好你自己,想想怎么交代问题。”
他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颗脑袋我不要了,你有种就拿去。我累了,走不动,哪儿也不去了。”
关键时刻他对我们大耍无赖之举,死活不肯挪一下屁股。
“说你胖,你他妈的还喘上了。”我揪起他衣领将人整个提了起来,一路连推带踹恨不得拿枪顶着他走。
戴绮思不时回头观察身后的情况,她看了看日头,对我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早晚会被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