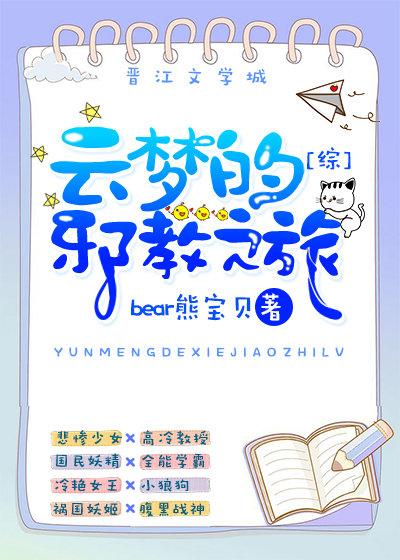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蕉鹿几事 > 第246章(第2页)
第246章(第2页)
边杨与花鞘蹲在农舍外。
“晚间回上梁,我不想在这了。”赵啟骛说。
“那向公子…”边杨踌躇着开口。
“你替我散消息出去,说我摔落雪山得少女相救,多日相处与她私定终身。”
“若向执安再来寻我,就说怕未过门的上梁世子妃闹脾气。”赵啟骛就睁着空洞的眼,低声说着话。
“向公子怕…怕是会伤心。”花鞘说。
“向公子若死活来寻世子,也瞒不过啊。”边杨小心翼翼的询问。
“那便与他说,若不是他动荡大晟,我父亲也不至于惨死。”赵啟骛的眼角清泪,清渣满脸。
“世子,这…太诛心了。世子,这不妥,为何非得作践向公子。”边杨语气里的埋怨渐重。
“怎,我这么一个废人,还有比我非要缠着他来的更作贱的吗?”赵啟骛淡淡的说“现下他已是国舅,而我再也不能为他守疆,玩谋算,我去那朝堂上滚一圈都能扎一身刺,玩行伍,我已前程尽断。”
“呵,本就是我仰望他,现在连仰望,都做不到了,更休说追赶了。”赵啟骛转身蒙被,不发一言。
赵啟骛回了上梁的消息顷刻间传遍大晟,但是比这传得更快的就是赵啟骛将向执安弃了,唯一被瞒得密不透风的就是赵啟骛盲了的事儿。
多方同时得到消息。
向执安听到消息不得其解。
入夜,赵啟骛说“寻个女子放我寝帐。”
深夜,向执安果如边杨所料策马进了上梁。
诛心的话自是没说,向执安的神情难以捉摸,是欣喜,还是迷茫,掺杂着疑惑。
向执安没通报,站在赵啟骛寝帐外许久。
手悬空中楞了许久,叩门。
传来女声“这么晚了谁呀?世子殿下已经睡了。有事儿明日再说。”
向执安一怔,按住颤抖的声说“劳烦姑娘叫醒世子,我有几句话想问。”
赵啟骛的声音很是熟悉,一如既往的轻浮,说“执安是要与我们一起玩么?”
“讨厌。”女子的调笑声刺耳。
向执安呆呆的立在门外。
向执安说“赵啟骛,我不信。”
赵啟骛说“门未锁,进来吧。”
向执安手指轻轻推开门,二人的衣物落了一地,能看见赵啟骛的脊背,怀里还有个女子,青丝撒在赵啟骛的小腹,从前那个装着给自己信件的锦盒被扔进了女子的肚兜。
向执安站在门外,这屋里的春情一览无遗,赵啟骛眼蒙着黑布,转过身来,撑着脑袋,下衣不整,暴露出大块儿的腿根,上头的伤痕清晰可见,又对着向执安调情似的说“执安,来,蒙着眼玩更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