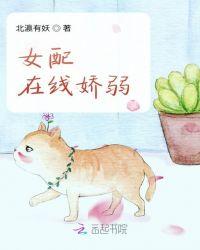墨澜小说>虐文求生游戏 > 第 210 章 大朝会(第1页)
第 210 章 大朝会(第1页)
是夜,大雨倾盆,清风县的小镇外忽然来了一队过路客商,为首的几名精壮汉子身着黑衣,头带斗笠,在前方策马开路,最后停在了一家气派的山庄前叩门。
“笃笃笃!”
“笃笃笃!”
雨声嘈杂,淅淅沥沥击打在屋檐上,形成一片连绵不绝的雨幕,年老的管家听见动静撑着油纸伞走出屋子,步伐蹒跚,褐色的衣衫很快被溅得潮湿:
“来了来了,谁在叩门啊,都入夜了。”
庄门打开,只见外面站着两名精壮的汉子,他们对管家拱拱手道:“老人家,在下乃神京来的客商,家中小主人身患重症,听闻神医陆家的一线针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奇效,愿献万金,诚心求医,还望代为通传。”
“轰隆!”
一道雷电猝不及防划开天幕,眼前顿时亮如白昼,只见那朱红色的大门上方有一牌匾,四个鎏金大字被照得清晰分明——
至微山庄。
世间医者多如过江之鲫,成名者却只在少数,而且或多或少都有些怪癖,什么必须以至亲之人的性命来换啦,什么必须万金以酬啦,什么看不顺眼的不救,不一而足,唯有神医陆家治病不问贵贱贫富,且家传的一线针法冠绝天下,只是世代隐居汝州,鲜有人知。
“原来是求医问药,好说好说,我这便去通传老爷夫人。”
身患疑难杂症慕名而来的人,老管家每天不遇上十个也有八个,陆家规矩是不得擅拒,便依照规矩将人引入了外厅招待。
这伙客商为首的是名中年男子,气度不凡,旁人称他为尹老爷,另还有名年迈的家仆抱着重病的小主人,瘦瘦小小的孩童,裹在狐裘被褥里看不清脸。
他们进入厅中的时候,只见一名十来岁的孩童正坐在餐桌旁捧着碗吃饭,眉目清秀,宛若璞玉,众人看清他的面容,都不由得惊了一瞬,面面相觑。
尹老爷捋着胡须,惊疑不定看向那孩童,须臾又收敛神色,状似不经意向管家打听道:“老人家,既已过了晚膳时分,怎么还有一名小童坐在此处吃饭?”
老管家笑着拱了拱手:“这是我家少主人,因今日贪玩未完成课业,便被责罚不许吃饭,谁曾想到了晚间夫人又不忍,使人悄悄热了饭给他。”
尹老爷点点头:“原来如此,小郎君生得玉雪可爱,贪玩些也没什么。”
老管家笑得慈祥,一副与有荣焉的样子:“我家少主人自幼聪慧,生来有过目不忘之本领,七岁熟读四书五经,八岁熟读诗词歌赋,如今十一岁已将家传医书针谱倒背如流,少年心气高,便不肯老实坐在书屋里。”
那尹老爷又是一惊,暗自赞叹:好聪慧的少年郎。
少年离得远,只低头安静吃饭,旁人说什么他也不理,吃完了不需丫鬟伺候,自己就捧着碗去后厨了。
他们一行人在大厅内坐了盏茶功夫,便有一丰神俊朗的年轻男子携一美妇出来,尹老爷起身拱手:“敢问可是神医
陆无恙?”
陆无恙客气还礼,他见这伙人虽自称过路客商,但腰间佩剑,明显功夫不凡,料想来头不简单,心中不免多了几分顾忌,但对方既已经寻上门来,再想推拒却是不能,不如尽早医好让他们离去:
“神医不敢当,请问诸位是谁要求医?”
尹老爷示意家仆抱着孩子上前,言语间难掩忧心:“便是在下的幼子,他先天心肺不足,我遍寻名医替他延续春秋,如今也已经力竭,还望神医搭救,我等必有厚报!”
陆无恙示意夫人去准备针药,上前将那孩童接到怀里,只见是个身着锦袍的富贵小郎君,呼吸微弱,唇色发紫,连喘息都费劲,全靠那家仆以内力助其运气,心中不由得一惊——
却不是因为他的病,而是因为这小郎君生得竟和刚才坐在桌边吃饭的那位少年有九成相似。
陆无恙微不可察一顿:“小郎君症状不轻,先入药室诊脉吧。”
尹老爷自然无不应。
那美妇去拿了银针滚酒,途经廊下时不知想起什么,对着小厨房柔声道:“延儿,时辰不早,早点歇息,莫误了明早的课业。”
语罢这才掀起帘子步入内室。
陆延蹲在厨房里把自己的碗筷洗了,这才转身准备回屋,那队客商除了尹老爷和几名家仆在里面,余者都在廊下等候,黑压压的一片人影,腰间佩刀,气势不俗。
那群人中间站着名三十岁许的男子,衣着朴素,面容英武,他负手而立,望着外间阴雨连绵的天色兀自出神,间或夹杂着几声低咳,视线不经意一瞥,忽然发现刚才在屋里吃饭的少年正站在走廊不远处望着自己,一时来了兴趣,对他招手道:“小郎君,且来。”
陆延却没立即过去,而是搬了两张小圈椅过来放在廊下,那男子下意识拦道:“不必了,在下只是见小郎君有趣,想说说话罢了。”
陆延歪头问道:“难道不许坐着说话吗,一定要站着说?”
男子闻言一愣,随即笑出了声:“许,自然许。”
他语罢果真掀起衣袍下摆,和这少年排排坐在了廊下,陆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花生,低头一边剥一边吃,偶尔抬头看看花园里的落雨,颇为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