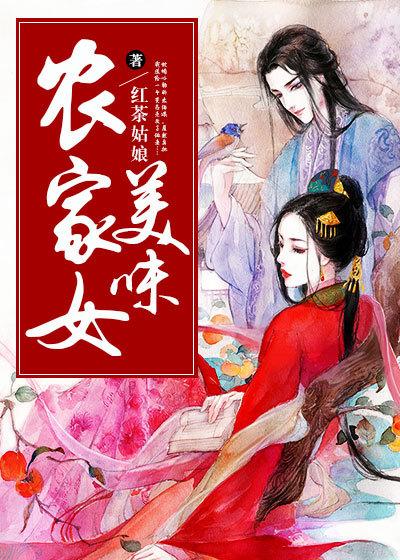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与秋 > 第十三片落叶(第1页)
第十三片落叶(第1页)
季时秋自小善水,但天气平等无人性,不会给他的勇猛以优待,当晚回到民宿,他开始打喷嚏,免不了吴虞好一顿冷嘲热讽。
他假装没听见,抿着白开水挨窗看山景。
丝巾没有与其他换洗衣物晾一起,而是被吴虞挂晒在窗沿,随风飘荡。
季时秋为这种区别对待而自得,想笑的时候就托高杯子掩饰下半张脸,等恢复正经再放下来。
但到了夜里,他没料到丝巾另有用途,它可以成为吴虞身上的雕饰,也能成为束缚他的镣铐。
他施展不开手脚,也彻底为她所用。
这种体验前所未有。
翌日清晨,吴虞是被季时秋烫醒的,男生坚硬的身体像个火坑,她不耐地动了动,后觉地用手背探他额头。
死东西。
吴虞暗骂一声。
季时秋烧得很厉害,腋温直逼四十度,吴虞把水银温度计搁回床头:“我下去问问林姐卫生院在哪。”
季时秋却很抗拒:“不去。”
吴虞只能去楼下问林姐是否有退烧药。
林姐翻了些乱七八糟的药盒出来,嘀咕:“也不知道过期没有。”
吴虞挑拣着,选出感冒冲剂和止痛药:“死马当活马医了。”
林姐笑说:“昨天我还没问呢,小秋掉水里了?”
吴虞呵了声:“嗯,傻不拉几的。”
她没有见过比季时秋更蠢笨的人,船就在旁边,明明有那么多方法可以寻回丝巾,最不济是放弃,而他却不假思索地下水,以身犯险。
季时秋坐在床边,将胶囊和水吞服下去,又被吴虞按回床上躺好。
他说:“我想起来。”
吴虞问:“你头疼不得了?”
季时秋不硬撑:“疼。”
吴虞说:“那就好好休息。”她起身拉上窗帘,让房内灰暗适睡。
季时秋没再吭声,他浑身炙烤,头痛得想把脑袋立刻摘掉,但他分毫不后悔。
缓释片起效没那么快,季时秋辗转反侧,闭眼良久,却怎么都无法安睡。
回到桌边玩手机,几次掐灭烟瘾的吴虞留意到,眼一挑:“睡不着?”
季时秋默认。
吴虞放下手机,破天荒地说:“我可以唱歌给你听。”
季时秋的身躯明显一顿,似是没想到。
“不想?”
“你唱。”
吴虞略一思忖,唇瓣微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