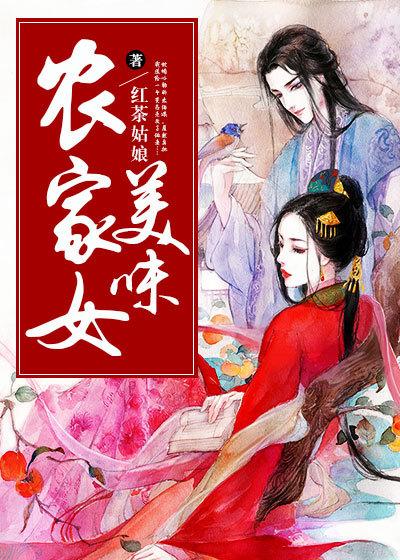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窝心 > 第53章(第2页)
第53章(第2页)
或许他早就分不?清恨的到底是宁初,还?是那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停止深爱的自己。
大洋彼岸的国度,明明不?需要亲自去的地方依旧在过去几?年被一次次踏足。
无数次隐匿于一座城市,明明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却?始终不?肯动动手指去寻找一下。
到底是憎恶到不?想看见,还?是不?敢看见。
他可以花时间去接受宁初忘记一切,可以忍受一个人背负那些?破烂残缺的记忆,反正早就卑微惯了,只要狠下心肠对待自己,没有什?么是不?能忍受。
他愿为自甘堕落将自己匍匐到尘埃,可就是有人非要将他拉起来。
他忍不?住去责怪宁初,既然已经想不?起来,为什?么非要得到一个究竟,就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不?好吗?
不?知道的时候还?会偷偷靠近他,藏着偷偷摸摸的欣喜跟他说话。
如今知道了反而?对他避之不?及,走路都恨不?得能在家里多?开辟一条小道绕过去。
可怪着怪着,最后罪责还?是会落在自己头上。
都是假的。
骗来的安宁就是高空坠落后的玻璃球,表面?完好无损,剔透的躯壳下早就爬满裂缝,指不?定碰到哪就会碎成一地。
明明是自己贪心不?足,明明早就已经意识到不?管如何,都回?不?到从?前了。
宁初没有回?答,也答不?出来。
他听出了今今话音里沉郁压抑的情绪,却?笨拙又沮丧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低头看着杯子里晃动的水纹,在晦暗蔓延的客厅保持沉默。
禁锢在手腕的力道忽然松了。
他仓皇抬头,却?只能看见清瘦的背影消失在走廊。
晕黄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模糊得像是快要碎掉。
从?猫舍回?去那天?起,或许是因为该暴露的都已经暴露了,宁初不?再被拘与?一隅,可以自由出入行走。
被关着的时候老想出去,现在能出去了,他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几?天?后,他一个人无所事事在家里枯坐了一上午,然后拿起手机,第一次独自离开了家门。
他想再回?去看看。
公交车的路线重新?规划过,他带着口罩,站在站牌前半天?看不?明白,最后还?是以为老大爷好心给他指路。
先坐108路,三?站之后换乘96路,坐到终点站。
上车之后,他挑了个靠窗的位置,路线不?认识了,窗外面?的建筑也不?熟悉了,他乘车穿梭在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觉得哪里都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