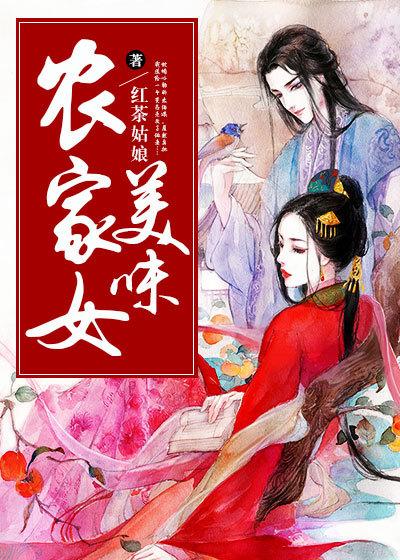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世子他为何如此黏人 > 第130章(第1页)
第130章(第1页)
柳筝指尖一颤,刚剥出?来的坚果仁掐断了,尖利的果壳刺进了她指腹里。
顾寻真惊得去拿她手,还没?握上就被宋砚紧张地牵了过去。柳筝没?什么反应,他手却抖了,拿了帕子尽量镇定地帮她把果壳碎屑从伤口里拨拢出?来。
沈氏的话还在继续:“……要?说不容易吧,这窑姐儿是不容易,受了不知多大的罪,才把这孩子顺利生下来。要?说她自甘堕落,也是真真堕落!你?们说说,好好一个人?有手有脚的,做什么不行?非得赖在那楼里过活,不还是贪图那烟花地的繁华光鲜?”
“我看也是!还说她痴情呢,我是没?看出?来,真痴情能一点儿廉耻都不要?了?再苦再难,能忍得了有第二个男人?近她的身?分明是本性为淫,还拿日子艰难做借口。”
有人?小声道?:“还有许多姑娘在呢,聊这些不太好吧……”
“都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多听听这些于她们没?坏处。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如咱们后宅里那般干净的。”
柳筝指尖的伤口不深,血却冒个不停,宋砚将她指尖放入口中含了含。感觉到?那一片濡湿,柳筝骤然回神:“别弄,你?碰不得血。”
宋砚唇色微白,有血润在了他唇线上,看着格外明显。他紧皱着眉头,松了唇拿干净帕子把她手指先裹住,牵着就要?起身:“先去上药。”
“不妨事,一点小伤就别大惊小怪了。”柳筝坐在原位不动,眼睛却盯向了那边还在叽叽喳喳说笑着的贵妇人?们。
“常说沽名钓誉者最讨人?嫌,这窑姐儿也是个心机深的,她挺着肚子,恩客们当然更尽兴,给的赏钱就多,她把赏钱掰了两半,一半自己留着,一半攒了叫人?寄给那书生去,盼着他考取了功名回来为她赎身娶她做夫人?。”
妇人?们哄堂大笑:“这不是狭恩图报么!哪个好人?家能要?她做夫人?啊!别说中了举人?进士的官老爷了,就是咱们家的小厮,也瞧不上这等?脏物!”
罗净秋悄然走来,轻轻按住了柳筝的肩膀。
可柳筝的视线已经模糊了,终于在听到?“脏物”二字的时候她再忍不住了,一掌拍在桌上起身:“够了!”
堂上静了片刻,众人?纷纷回头看她。
宋砚一直关切着她手上的伤,此时才注意到?她情绪已濒临崩溃了。看到?桌面?上从她指腹里晕开的血和她眼眶里含的泪,宋砚心尖抽痛,面?如冰霜地扫向了席间众人?。
他方才并未细听闲人?话语,只隐约听到?什么秦淮河、窑姐儿几个刺耳的字眼,还不知道?柳筝具体在为什么气愤,但这些个贵人?以赏花为名聚集起来开办雅宴,谈来谈去尽是这些内容,何等?讽刺虚伪。
他看向罗净秋,期望能从她口中得到?答案,罗净秋摇了摇头。
席上妇人?们相视一笑,沈氏看着柳筝笑道?:“好端端的,柳姑娘这是怎么了?难不成?咱们聊咱们的,还碍着你?的事儿了?”
柳筝抑了抑喉间的哽咽,忽而笑了:“你?的本意便?是要?羞辱我娘,羞辱我,何必绕那么一大圈子呢。我是没?什么见识,自小在市井里长?大,听不明白你?们这些权门贵戚口中的弯弯绕绕。”
“柳姑娘想的也太多了,”沈氏无奈一笑,“我们在说秦淮河的事儿呢,哪里就扯到?你?身上了?”
“是啊是啊,你?激动个什么?”妇人?们捂嘴笑起来,“难不成?你?也是那行院人?家出?身么!”
坐在上首的秦老太太一脸轻蔑。年轻姑娘就是沉不住气,稍微激个两下就坐不住了。
“你?口中的那个窑姐儿,是我娘柳絮。我娘有名有姓,她叫柳絮,不叫窑姐儿。她不是天生下贱,不是本性为淫,不是狭恩图报有意沽名钓誉者,更不是脏物!”柳筝深吸一口气,嗓音清亮,“我娘活得坦荡,既注定要?承受骂名,她坦坦荡荡地受着,你?们既然要?骂何必还假借一个他人?的由头?”
“沈夫人?,”柳筝目光灼灼,“我知道?你?们一定特地查过我的身世,我娘的过往你?们都心知肚明,所以才在这等?场合上玩笑似的提起这桩往事。你?们怎样看我、想我,我都无所谓,我柳筝一直都过的是我自己的日子,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样子。可我不明白你?们羞辱一个沦落风尘的母亲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你?们应该知道?贬损别人?、羞辱别人?,把别人?骂得一文不值,也并不能衬得你?们本身有多干净高贵吧?你?们的心才是最脏的。”
“哎呦呦,是我犯糊涂了,谁想到?原来柳姑娘你?的母亲竟是,竟是那般出?身啊……这,说个故事,怎么这么巧就说到?你?头上来了呢?”沈氏忙笑着打圆场,端了杯酒到?她面?前?来殷切道?,“我给你?赔个不是,这按辈分,其实你?该叫我一句三婶婶呢,婶婶说错了话,谅婶婶这回好不好?”
顾寻真气得想为柳筝出?头,被罗净秋拉住了想自己来。宋砚抬袖挥开了沈氏手里的杯盏,想将柳筝护到?身后去。柳筝挡了他的手,也拦住了罗净秋,仍直视着沈氏的眼睛:“为何要?吞吞吐吐,我娘那般出?身,是哪般出?身?你?刚刚不是说得很有劲头么,怎么到?给我道?歉的时候,就说不出?来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