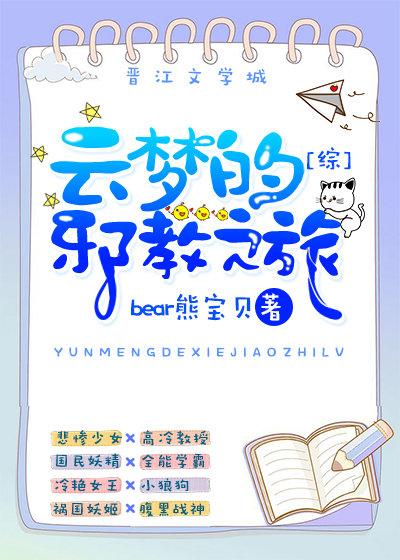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纨绔夫妻 > 第一百五十章(第1页)
第一百五十章(第1页)
:
付忱这一刀断情绝爱。
李在心中再疑接住管事的一招后,避让后退,不敢拿一县长官的性命开玩笑。
管事满脸喜意,狞笑一声:“我们两条贱命,换狗官一命倒也划算。”
“走。”付忱挟持着时载,低喝一声。闻讯而来的牛叔看着恼怒异常,狠狠地瞪了李在一眼。李在心里悔过参半,他私心觉得自己也不过这当口大意了一点,让付忱擒了时载为质。
牛叔执刀道:“这位好汉,切勿轻举妄为,你二人……我看小兄弟武艺粗疏,真若错了手,此趟怕走不脱。”
付忱道:“这却要赖怪你们,我与管事好好地来栖州城看看有无买卖可做,这位却要将我们当贼拿,既担了贼名,不行恶事,岂不是辜负了你们的美意。”
李在怒道:“胡扯,在江上见你们就是鬼鬼祟祟的模样,自己是贼,倒还来占这等口舌便宜。”
付忱轻笑:“你们真个要和我较论长短,我听闻一人的血,拢共也就□□斤,这血流光了,付县令的这条命怕是因为你们这些大头兵,交待在这。”
牛叔道:“你待如何?”
“求去。”
“好。”
李在急道:“叔……”
“闭嘴。”牛叔一挥手,喝止两边手下,又清出一条道来,“放他们走。”
“识趣。”付忱赞道,又使了个眼色给管事。管事劫了旁边商客的两匹马,付忱抓着时载翻身上马,管事对着马屁股狠狠一记,吃痛的马嘶鸣一声,扬蹄狂奔。
牛叔叫人赔了商客的马钱,自己领着李在等人急追出城,时载手臂的伤口血流如注,一路撒向城门口,马蹄踏上,溅出万点飞红。
时载失血过多,被横放马背上,五脏六腑都快要被颠簸出来,恍惚中听付忱道:“对不住了。”巨痛之中,似身回幼年之时。
其时他年岁尚幼,被他娘亲牵着手,翻山过水,走得两条腿几要断掉走到了桃溪。烟雨迷离的水镇,绿柳堆烟,道上铺着青石板,雨天走道,急慌了能摔他一跤。他娘亲是带他来投亲的,心中没底,紧紧攥着他的手,攥得他手生疼,也不顾他年幼力乏,几次都拉得他险些跌倒,就这般踉跄蹒跚,总算到一户富贵人家门口。
他抬头,门上挂着桃符,门口站着门子,见他们形容狼狈,也未曾露出轻鄙之意,只叫他们在门外等侯,容他进去禀报家主。
他嫌亲忐忑不安,抿了抿凌乱的发鬓,又用力将他身上尘污拍了拍,道:“我们来走个亲戚。”
这是自欺之语,他们是上门打秋风。
也不知过了多久,许是风歇的功夫,又许是过了几盏茶,大门重又打开,一个衣裳鲜亮的管事牵着一个生得俊秀玉白的小郎君出来,口中大为无奈地念道:“小郎君,只你又顽皮,出来作甚。”
“我来看看的什么亲戚?”小郎君笑嘻嘻地说。
“你小小年纪,人都认不全,看了又能知得什么亲戚?”管事笑起来。
小郎君却是个任性的,一把丢开管事的手,跑到他的面前,将他左右端详了一番,嫌弃道:“你可是跌跤了?这么脏!”
他缩了缩手,自惭形容不堪。
谁知,那小郎君嘴上嫌弃,却又嘻笑地牵了他:“你陪我玩去,你见过虫戏没有?我叫小厮耍虫戏给你看,他能招来一串蝶。可惜现在下雨,那些蝶儿也不知去了哪去,明日天晴,我们再看。”
他……许久未曾见过虫戏了。时载模糊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