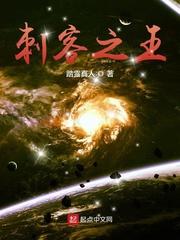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总有老师要请家长 > 第50章 50(第1页)
第50章 50(第1页)
从教三年多,祁言没有遇见过恶心的事,前两天她仍这么想。但现实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
被领导喊去谈话的当天,祁言在办公室违心地保证自己会守口如瓶,不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甚至忘掉自己目击者的身份。杨清也是,那姑娘一宿没睡,要去看心理医生。
同时刻,跳楼学生的家长带着老人在校门口哭天喊地,拉起了横幅。老人家往地上一坐,要死要活的,保安只敢训斥威胁,不敢碰。
至于后来……
家长在校门口闹了一天,被请进领导办公室,第二天没再闹。各班主任严令禁止自己班的学生讨论这件事,想要采访的记者始终被拦在门外,起先外界说法各不同,最后统一口径:女孩不堪学习压力而轻生。
网络一片“现在的孩子就是脆弱矫情”的声音。
前后不到三天,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翻起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水花很快就平静了,生活依旧,教学秩序也依旧。
附中还是附中。
只是二班和七班突然换了数学老师,校园里没再见到徐首逵的影子,不知下场,不知去向,办公室里也没有老师谈论,好像事情从未发生过。
有时候,祁言以为自己那天看到的是幻觉。
真的有学生跳楼吗?
真的死在她面前吗?
那双幽怨的眼睛,满地殷红的血,会不会是她精神错乱,从恐怖片里抠出来的记忆?
那天祁言回了父母家,林女士问起怎么回事,她看着母亲担忧的面孔,紧张的神情,忽然很希望再听几句让她厌烦的唠叨。她动了动嘴唇,拿出平生最棒的演技,灿然一笑。
“妈,没事,小孩子学习压力大,一时没想开而已。”
林女士保养得水仙花儿似的脸皱成了包子褶,果然开启了叨叨模式:
“现在的小孩儿都是宝贝,说不得碰不得,娇生惯养宠大的,这才多大就有压力了,往近了说,中考高考要竞争,往远了说,以后到社会上讨生活,有的是苦头吃,那动不动就跳楼吗?”
“妈,我不也是被宠大的么?”祁言笑着说。
林女士眉头一拧,摆摆手:“我跟你爸给你的是尊重,跟那些只会溺爱的家长能一样吗?”
“……”
“我跟你爸从不当你面吵架,外面遇到再恼火的事,也不回家撒气,以前没什么钱的时候,不在你面前强调咱们穷,也没动不动就要你记着我们多好多好,欠我们的。我问你,哪几个父母能做到这些?”
林女士说着说着,语气不由得自恋,嘴巴一噘,又有点不高兴,因为被闺女误会了,委屈。
“那些心理脆弱的小孩儿啊,都是平时溺爱出来的,我打个比方,就像笼子里的金丝雀,看起来很宝贝吧,好吃好喝供着,其实拴得死死的,哪儿哪儿都给憋的……”
有道理。
祁言若有所思地点头,笑着抱了抱她亲爱的老母亲。可林女士不罢休,抓着机会必定要撺掇一番。
“跳楼那个学生的班主任没事吧?哎哟哟,摊上这种事真是倒霉了,我看到网上说是班主任造成的,还有说是被数学老师骂了的,数学老师也倒霉。”
“言言啊,你当心点,对你班上的孩子呢能管就管,管不了就算了,又不是咱们自己的孩子,明哲保身懂吗?这一天天的出事,你还呆在那儿,妈都怕死了……”
林女士搂着闺女又是亲又是抱的,团子不高兴了,伸出一只爪子扒她胳膊,喵喵叫了两声。
没人理它。
祁言安慰地拍了拍林女士肩膀,笑容有些僵硬:“我知道,我会多注意的。”
以前她最烦听老母亲说这些,三句能顶十句,现在却想不到能用什么话来反驳。她有点累了,脑子还没缓过来,心上火热的温度也降了些,拿不出力气。
她想,她应该学着做一个聋哑人。
祁言向学校请了一周假,在家休息。
她住在901,晚上跟陆知乔同睡,自认为老实规矩,可每天早上醒来不是她在陆知乔怀里,就是陆知乔在她怀里。两人发丝缠绕,呼吸相交,彼此当对方的抱枕,适应得极好。
陆知乔工作忙,不能时刻陪着她,但尽量每天准时下班,偶尔两人一起买菜做饭,去接女儿放学。
俨然和乐幸福的三口之家。
温情与陪伴是治疗心里创伤的良药,祁言明显感觉自己的状态好了许多,闭上眼睛不会再想起那些画面,又或许是她自我催眠有了效果——是幻觉,看到的都是幻觉。
周末上午,陆知乔要加班,祁言在家陪“亲女儿”,打扫了一遍卫生,而后去买菜。差不多十一点,陆知乔回来了,两人一块儿做饭。
“我总觉得妞崽最近有点反常。”
她穿上新买的围裙,朝次卧望了一眼,那房门始终紧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