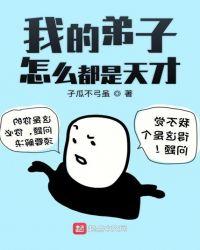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无敌透视 > 第254章 天地归位(第3页)
第254章 天地归位(第3页)
张全护着头,连声求饶:“别打了,别打了,你看在这只陶罐的面子上,也算我将功折罪嘛。”
一说到陶罐,茗心便停住手,从地上拣起陶罐,问:“你确信,它值几个钱?”
“何止几个钱!这个罐型,我从未见过,估计是个绝品。物以稀为贵,说不上能卖个天价呢。”
这一说,茗心倒有几分动容,把陶罐左看右看,竟然越看越喜欢。
“我明天就去找张教授,让他给看看,能不能在古籍上找点来路,给它命个名,价钱就提上来了。”张全说。
“又要付好多钱吧?”茗心说,“上次你托他替你的玉如意写论文,他可是要了你5万多元呢。”
“5万怎么了?那个玉如意,明明是清代一个王爷的,硬被张教授给考古考成了明朝皇帝朱元璋的,价格不是涨了几十倍嘛?”张全得意地说。
“也是,那你明天就跟张教授说,把这个罐子好好地‘考证’一下,年代越远越好,最好把它搞成开国皇帝的东西才值钱。”
张全用指手点了点茗心前身的两个点,嘻嘻笑着,“你是近墨者黑,跟我这两年,也快专业了。”
“你他妈跟我这两年,也没闲着,天天在外面混,也快成专业嫖客了。”茗心骂道。
张全嘻笑着凑近,把脸贴在她的脸上,闻着她贴身衣服领口散发出来的香气,“好闻,好闻,你这里的气,就像进了花圃,闻了就迷,恨不得立刻把你办了。”
茗心拉了拉前襟,故意把两个雪白露出来大半个,媚眼如电地瞟了张全一下,“你那德性,除了下面那点事,你还对什么感兴趣?”
张全也不答话,便把手伸进去,胡乱抚了一阵,抚得茗心娇而啼。
茗心被摆弄得心下又震荡起来,不禁大怒:“你他妈光添柴不烧火,老跟我玩虚,我今天把你剪下来。”
说着,从抽屉里抽出一把剪刀,冲了过来。
张全忙把陶罐捧在手里,迎着她的剪刀,说:“你小心,这可是古陶,不结实,碰坏了,一分钱也休想了。”
茗心倒是真心疼陶罐,便放下剪刀,撅起俏的臀,从张全手里拿过陶罐,说:“还真得好好收着。”
说着,一拧细腰,捧着陶罐来到收藏室,把陶罐摆在一个架子上。
在灯光下,陶罐黑乎乎的、灰蒙蒙的,并不雅观。尤其是开着口子,露出里面无粙的内胆,更显得土里土气。
茗心看了,说:“这罐子是不是原来有盖子呀?”
张全上前看了看,说:“很可能,因为口子上有盖沿,一圈儿。”
“要是有个盖子就好了,看着也舒服。”茗心说。
张全说:“我们给它加一个。”
两人找了几个盖子,都盖不上。最后选中了一个一个楠泥茶壶的盖子。那盖子不大不好,正好合适,把个陶罐盖得严丝合缝。
两人打量了一番,觉得不错,便回卧室睡觉了。
哪成想,这一盖盖子,可苦了里面的人了。(未完待续),!
张全一心侍奉茗心,以便掩饰自己的恶劣行为。但这种事不是能装出来,毕竟弹药不足,不到一个基数。
春江水暖鸭先知。那茗心是个中老手,如何觉察不出来。任张全再卖力气,她也知道他自己不过是打扫战场的角色了。
茗心被弄得不上不下,来气了,一脚将张全蹬下铺来。
张全没有防备茗心这招,就从铺上滚下来,在地板上打了几个滚儿,像那陶罐一样,滚到了墙角。
“哎哟,哎哟,”张全疼得直叫唤,捂着腰眼,咧着嘴。
“妈的,狼心狗肺的东西,老娘我跟了你,也不算高就了。你他妈三天两头现去找小的姐,回来还跟我装,装,我叫你装……”
茗心越骂越来气,挥起枕头甩过来。
张全用手挡住打来的枕头,“别介呀,我对你可是一片衷心呀,今天,确实身体不好,有点感冒,明天我一定补上这课。”
“补,补,补你个头。”茗心叫着,把肥软的身体从铺上跳起来,冲过来,对张全又踢又打。
张全护着头,连声求饶:“别打了,别打了,你看在这只陶罐的面子上,也算我将功折罪嘛。”
一说到陶罐,茗心便停住手,从地上拣起陶罐,问:“你确信,它值几个钱?”
“何止几个钱!这个罐型,我从未见过,估计是个绝品。物以稀为贵,说不上能卖个天价呢。”
这一说,茗心倒有几分动容,把陶罐左看右看,竟然越看越喜欢。
“我明天就去找张教授,让他给看看,能不能在古籍上找点来路,给它命个名,价钱就提上来了。”张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