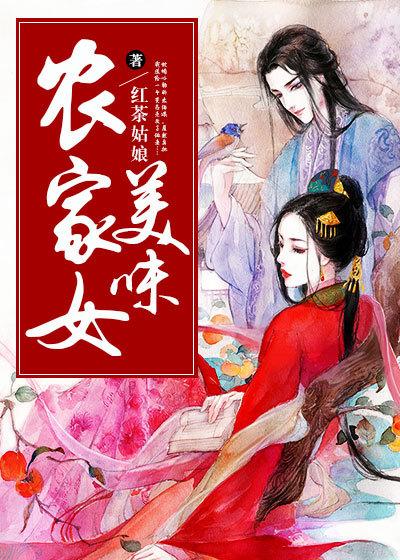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在武侠世界开奶茶店 > 第76章 第76章(第2页)
第76章 第76章(第2页)
另一方面,她脑子里现代社会依法定罪的念头还是没转过来,她已经是个三观定型的成年人,某些时候,她真的很难和这个世界融合进去。
但她更多的还是感谢无情和沈青,帮她把这些破事挡在外面,要不然有麻烦的就是她了。
她的视线不经意划过桌前的化妆镜,猛地一拍脑门,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急忙从背包拿出洞玄水镜,自从抽出来后,她还一次都没用过,想了想,她在意念里说到,傅宗书卧房。
波光粼粼的水面散去,就像在看电影一般,镜中渐渐浮现出几个忙碌的人影。
屋子里塞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几个一身官服的老人围着一张华丽的床榻,有个一直在诊脉,床上躺着一个人,但头刚好被挡住,她看不清面貌。
女人和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的传来,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衣着华丽的妇人,身旁跟着几个年轻男女,还有两个小孩子。
谭笑心里猛地一跳,这样的阵仗和待遇,除了傅宗书,再不会有第二个人。
看其他人的举止,这老贼现在似乎很不好,要么就是受了重伤,要么就是快不行了。
她屏住呼吸,想听清楚他们的谈话,此时,为首的妇人哭着问道,“张太医,我家老爷怎么样了?”
把脉的那人沉沉叹了口气,脸色凝重至极,他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开口,看上去为难极了。
“夫人,请恕老夫才疏学浅,傅相伤了心脉,能熬过这两日已是用药材吊着命的结果,如今恐怕是……”
话音一落,屋子里的哭声蓦地大了几分,说话的那女人更是一头栽倒在地,真是够乱的。
于是几个小辈又手忙脚乱地去搀扶,又有个看起来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扑上去冲着张太医拳打脚踢,恨声骂道,“你胡说,你这个老匹夫,是不是诸葛正我派你来故意把我爷爷治不好的!我爷爷是当朝丞相,皇帝见了都得礼让三分,你敢不尽心治,我现在就去宫里找官家告状,让他把你们你个老匹夫的脑袋统统砍掉!”
一旁哭泣不止的少女吓得立刻去捂他的嘴,小孩疯狂挣扎扭打,于是又有两人上去把他拉下来,年纪稍长的一个男子表情敷衍地道了声歉,“诸位太医,犬子顽劣,他不过是太过担忧祖父的病情,若是有无礼之处,还请各位不要跟小孩子计较。”
张太医表情难堪地整理好自己的衣冠,他强忍着怒气,勉强露出笑说道,“傅大人说得是,小儿之语,下官必不会放在心上。”
谭笑看得忍不住冷笑,这一大家子向来仗势欺人惯了,一个十岁的小孩这么侮辱当朝御医,当爹的也只是轻飘飘一句我家孩子还小你别跟他计较啊,你要是计较了你就心胸不宽阔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个专横跋扈的家长,教出这样的子孙再正常不过。
听张太医方才的话,傅宗书也没两日好活了,就是不知道等他死了,这一家子还能不能继续他们骄奢淫逸的富贵日子,反正她也没听说傅宗书的儿子有什么出息,总不能指望蔡京念着两人的友谊,对他的家人还特殊照顾吧。
才怪,人死如灯灭,傅宗书不过是蔡京的一条狗,傅家又不是什么老牌大族,哪来的底蕴。
等他一挂,他身后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只会被迅速清算,朝堂上多的是对他恨之入骨,哪怕死了也要踩一脚的人,他们一家能不能维持平稳的生活都说不定。
一刻钟的时间到了,镜子上的影像淡去,又变成了蓝色的水波纹。
也许是见了这么一场闹剧,她心里那点因为第一次伤人而起的复杂的奇异的思绪,这会已消磨得干干净净。
她紧紧咬着下唇,一手抓紧床单,眼神逐渐从迷茫,渐渐变得坚定。
有些人的恶,可以用律法使他赎罪,有些人的恶,就只能送他去地狱。
律法在这个逐渐崩坏的世界,从来都只是为王公贵族服务的,那些因蔡京和傅宗书作恶而被牵连的百姓,因他们的排挤和加害而死去的臣子们,因他们作乱而日渐凋零的国力,那些死在靖康之耻中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难道就白死了?
无情他们那样艰难,与蔡京一派斗了这么多年,他们不也是毫发无伤,可见正经的手段对这些人压根就没什么用,直接一刀捅死了事,早点送他们去投胎,就少祸害一个好人。
她从抽屉掏出一个小本本,上面记了无数的名字。
找到傅宗书那一个,她用红笔在名字上划了一道,然后又将本子上记录的人名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才心满意足的合上放进抽屉。
突然就有种未来可期的感觉了呢。
作者有话要说:
哎嘿……我还是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