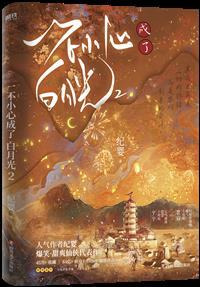墨澜小说>1356782 > 第 1046 章(第2页)
第 1046 章(第2页)
手术从晚上一直进行到天光,红灯熄灭,护士推着沉睡的沈钰从手术室出来。
床边挂着点滴,沈钰身上只盖着医院薄薄的被子,假使右手没有厚重染血的纱布,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凑上前,趴在病床边,他脸上有几处小的擦伤,却一点也不影响他五官的雅痞,甚至为此添了几分硬汉的气质。
眼睛忽然就红了,吸了吸鼻子,抬头问医生,“大夫,我哥的情况怎么样?”
经过一夜手术,医生的脸色并不算好,有些疲惫的点了点头,“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不过,”医生欲言又止,“宋太太,沈先生的右手是断裂伤,后期需要进行接骨手术,另外,虽然送医及时,手臂的肌ròu组织还是坏死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就算复原,神经是无法复刻的。。。。。。”
“就是。。。。。。”我做了个吞咽的动作,将紧张情绪都咽下,强装镇定,“以后右手,不能用了是吗?”
医生叹了口气“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可能性很大。”
“您要有心理准备。”
说完,便带着护士走了。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高跟鞋“嗒嗒”的声音在走廊响起,伴随着小碎步的声音,莫菲林急匆匆赶来,看了眼双门大开的手术室,把手搭在我肩上,“还好吗?”
我再也忍不住,抱住她哭了出来,“沈钰的右手坏了,永远都治不好了!都怪我!”
或许人总是要亲眼见证至亲受伤受辱,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没用。
让人无能为力的,除了感情,便是生老病死,感情我给不了,还让他为我搭上一只手,我彻底没了主张。
看见宋予安的时候,我从没有任何一刻对他如此的失望和气愤,甚至连哭声都戛然而止不愿叫他见到,“你来这儿做什么?”
不等他回答,又自说自话,“替慕容谨来看我们的笑话?你的目的达到了,可以走了。”
我无数次想要从恶魔身边拉回来的人,现在却要亲手推开,心里又何尝能够好过。
可我没有办法,没办法忍受宋予安像个陌生人一样的冷漠,至少,不是在沈钰昏迷不醒的时候。
我讨厌任何人,包括我自己,仿佛全世界都是加害沈钰的推手,
宋予安不为所动,薄唇微张,“沈钰太鲁莽了。”
“什么意思?”情绪上头的时候,任何一点细枝末节都会无限放大,他的话深深的刺激了我,我毫不犹豫的恶语相向,“你是说沈钰自作自受说他活该是吗?”
宋予安紧闭双唇,没有接话,莫菲林在旁边劝架,“宁桃你冷静点。”
“我还要怎么冷静啊。”我忽然好绝望,没有人能懂我有多煎熬,我既不能在这时候,理直气壮的将全世界最恶毒的话用在宋予安身上,也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只顾着自己是否能找回心中所爱。
我害怕那些恶毒的话真的会把宋予安彻底推给慕容谨,也害怕为了私心将沈钰的伤大事化小辜负他付出的一切。
宋予安和莫菲林似乎真的无法理解我的心情,一个神色如常,一个面带怜悯,让我更清楚的意识到,他们无法与我共情。
“算了。”我泄了气,作出让步,红着眼睛抬头看向宋予安冷漠得像淬了冰的眸子,“你说沈钰莽撞,那你呢?”
我逼近宋予安,脸几乎贴着他的,“这么多年还是喜欢独自行事,你还当现在是从前,觉得这样做很伟大是吗?!”
走廊里都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