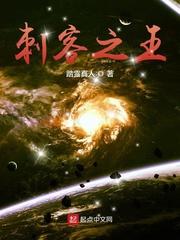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喜春来 > 第 204 章(第2页)
第 204 章(第2页)
俞峻平静地问:“说了什么?”
张幼双一边说着,一边笑着把牡丹绢花往俞峻头上戴:“说你昔日可是不愿人往他鬓角簪花的,还是旁人劝说皇命难违,这才簪了一朵。”
“我的确不喜男子簪花。”俞峻看了她一眼,温驯地垂下眼,任由她动作。
他到底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古板,不喜男子簪花。
俞峻眸色沉静如昔,秋水潋滟,如玉的肌肤,愈发衬得那花艳,那鬓角乌墨的黑。交织出惊心动魄的艳色美感。
许是有点儿不大适应,又许是因为打破了自己的原则,俞峻他眉梢微微蹙起。但这两条细长的眉毛拧起,却愈有种惑人心魄的反差感。
看得张幼双心脏再度狠狠地不争气地抽了两下,面色烧红地搁下了手。
她还记得刚刚恩荣宴上,那些官员是怎么笑着调侃俞峻的。
什么冷面财神,什么朝中刺头,什么古板的大家闺秀,玉女似的人物。
所以说禁|欲的人纵|欲,古板的人出格,才是最刺激的,果然诚不我欺。
这一路上,张幼双脸上都有点儿烫。
就在这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个惊疑不定的嗓音。
“俞……危甫?”
俞峻牵着她的手转了个身。
对面站着两个官员打扮模样的男人,看到张幼双和俞峻,都懵了。
“竟然真的是你?”
这两人的目光惊诧地落在了俞峻的鬓角,眼里满是掩饰不去的震悚。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会遇到昔日同僚,俞峻怔了一怔。
张幼双敏锐地察觉到他握着自己的手紧了一下,面上依然一派平静,除却耳根微红。见状,她差点儿笑倒在了大街上。
至于那朵绢花。不过几文钱,却是戴了一整晚,直到第二日方才取下,置于匣中,这般妥善保存了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