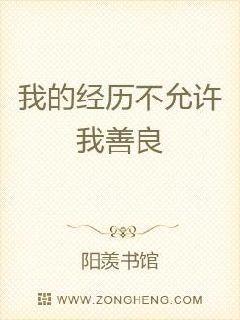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皎娘 > 第222章 姐弟终重逢(第1页)
第222章 姐弟终重逢(第1页)
只不过,这些事都不能说的太明白,但主子心里却是有数的,故此,同贵儿这几年熬下来,往后在侯府也就站稳脚了。
想到此,便道:“等燕州府回京您便来侯府吧。”
不想同贵儿却道:“正想跟大总管说此事,奴才想留在状元府。”
李顺儿一怔,真没想到同贵儿会这般打算,状元公府虽好,可跟侯府却也没法比,说到底是寒门出身,即便高中状元,想熬到封侯拜相也不知哪辈子呢,更何况,就算状元公日后入了阁,成了朝廷大员,跟代代勋爵的忠勇侯府也没什么可比性,要不怎么说世家大族呢,说白了,即便在侯府做个看门的也比在状元府当管事更体面,这就是差别。
正因如此,同贵儿如此选择,才让李顺儿颇为意外,不过意外归意外,这样的同贵儿却让人不得不高看一眼,毕竟这年头,谁不是削尖了脑袋钻营,有现成的高枝儿可攀,谁不是上赶着,偏偏同贵儿不一样,作为下人,有情有义,一样令人敬佩。
李顺儿点头道:“得空我便跟六爷回禀,你安心吧。”
同贵儿大喜,郑重给李顺儿鞠了个躬,转身去了,积在心里五年之久的一块石头终是搬开了,从今儿往后他就一心一意的侍奉状元公了,想到此,脚步格外轻快。
进了舱房,见冬郎正拿着书坐在窗前,便去端了茶水来,放到他手边的小几上,可冬郎却仿佛没看见一般,目光直愣愣落在书上,却看不进去一个字,脑子里晃过的都是过去在家时的事,阿姐教他写字,教他画院外的葡萄架,阿姐精神好的时候在窗前绣花,自己在旁边描红,或许正因这样的时候不多,所以他一直记着,从不曾忘。
也正因此,他恨梁惊鸿害了阿姐,这五年里他真以为阿姐不在了,却怎么也没想到,阿姐竟然活着,到这会儿,他都觉着像是做梦,他不是做梦吧,不行,他得找个人问问。
正好看见同贵儿,遂一把抓住了他:“同贵儿,你说我是不是做梦了,我阿姐真的活了吗,她真的活着吗?”
同贵儿忙道:“是真的,真的,大娘子活着,这会儿就在上面的舱房中。”
得到了肯定答案的冬郎,终于相信不是自己做梦了,喃喃的道:“是真的就好,就好。”放开同贵儿却见他跪了下去,不禁道:“你跪什么?”
同贵儿道:“公子,事到如今也不能再瞒下去了,其实五年前我便知道,入了葬的尸首并非大娘子,别院出事的时候,我并未出门……”同贵儿把当年的事和盘托出说的甚是仔细,说完五年前燕州的事,又说京里:“因公子执意去玉佛寺,小侯爷不放心,又因奴才侍奉过公子,便借着由头把奴才赶出来,投奔公子,是我骗了公子,公子责罚我吧。”
冬郎看了他良久道:“想来你也知道,你若不说,我亦不会揭穿你,为何今日要说出来?”
同贵儿:“我,我想以后一直跟着公子,侍奉公子,既如此,便不能有所隐瞒。”
冬郎:“跟着我有什么好,你这般机灵,若回去侯府必能得主子重用,岂非比在我这儿强的多。”
同贵儿忙摇头:“我已经跟李总管说好,以后便一心侍奉公子,公子打我,罚我都好,就是不要赶我走。”
冬郎叹了口气道:“起来吧。”
同贵儿一呆:“公子不罚吗?”
冬郎:“当初你本就是侯府的人,为他做事听他差遣是你的本分,我罚你做甚,不过,你既不愿意回侯府,非要留在我这儿,以后若再犯错,可就真要罚了。”
同贵儿仍有些忐忑的道:“那,那公子也不敢我走了吗?”
冬郎摇头:“如今状元府上下都是你管着,把你赶走了,难道要我自己管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