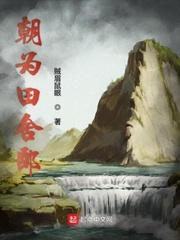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抗日之英雄传奇 > 第八百八十四章好赌的武藤生(第1页)
第八百八十四章好赌的武藤生(第1页)
“武藤生就是这么教你说话的?”江淮眉头一皱。这群人非但不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反倒像是一群地痞流氓,不过是见过生死的地痞流氓罢了。
“我们保护你是给武藤生将军的面子,可不是给你这么一个小小的少佐面子,你最好搞清楚这个事实。”
“公鸡戴眼镜。”江淮突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迈步便往军政部的大楼走回去。
“什么意思?”几个人听的莫名其妙,这难道是中国人的什么暗号吗?
“官不大,架子不小。”
“你给我站住!”终于有人听懂了江淮的话,气急败坏,大
喝一声冲向江淮,右手成鹰爪型,径直抓向江淮的后背,前冲的阵势带起一阵恶风,袭向江淮。
江淮毫无察觉似的,侧过身低着头,手挡在火机上,慢悠悠地点燃了手里的烟。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江淮这一侧身,却躲开了那人狠戾的一抓,那人重心不稳,顿时踉跄两步,险些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地上。
“咦?你怎么摔了?就你这身手还保护我呢?赶紧洗洗睡吧。”江淮故作惊讶地看着他,有些不屑地嘲讽他。
江淮这一嘲讽,周围几人顿时大怒:他们都是武藤生的私人武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江淮嘲讽袭击他的人,无异于嘲讽了所有人。
几人虽然暴怒,却并不像街头流氓一般喊打喊杀,雷声大雨点小,整齐无声地冲向江淮。
江淮正好有意试探一下这些人的实力,当下将燃着的烟头放在旁边的石墩上,活动着身体,走向几人。
“将军,你的这个心腹,有些太过高傲了啊。”武藤生的办公室里,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站在窗口,和武藤生并肩而立,看向操场中的闹剧。
武藤生哈哈大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样,老朋友,要不要赌一把?”
“赌什么?”中年男人一挑眉,从兜里摸出一叠银元,也不问武藤生想赌什么,放在窗台上。
“当然是赌他们的输赢了啊,我压江淮,你呢?”武藤生嘿嘿笑着,也掏出银元放在窗台上,一个简单的小赌局就此展开。
“我肯定赌我自己的部下啊,看着吧,你这次输定了,就和
以前一样,你总喜欢将赌注押在势单力薄的一方,所以你经常输的很惨。”
“可是我赌输只限在赌桌上,在战场上我可从来没有赌错过。”武藤生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看的中年男人有些心虚。
两人在上面兴致勃勃地赌博,下面却已经打开了花。
江淮不得不承认,武藤生的私人武装还是有点用处的,这些人单论个人实力,拍马也赶不上江淮,但是这几人攻守有度,阵型丝毫不乱,压得江淮有些喘不上来气。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纵使江淮手眼通天,能用上的也就是双手双脚而已,而对方却不同。
中年男人见状大喜,沾沾自喜地掂着窗台上的银元,余光看着脸色有些阴沉的武藤生:“看来某人又要输了哦。”
“还没完事呢,鹿死谁手,不也得看个究竟么?”武藤生看
着苦苦招架的江淮,不信邪地说。
“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还是老样子。”中年男人摇摇头,看向下面,顿时瞪大了眼睛,一声惊呼:“怎么可能!”
两人交谈的时间不过须臾,下面的战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围攻江淮的五个人现在已经有两个人躺在了地上,剩下的三个人也被突然神勇起来的江淮压着打,原本固若金汤的阵型顿时变得涣散。
江淮刚才眼见招架无力,突然想起了之前和赵凌云探讨切磋的时候。
“四哥,如果有人围攻你,你会怎么冲出去?”那时的江淮擦着满头大汗,坐在石桌上看着努力举石的赵凌云。
赵凌云将手中的石头放在地上,砸出咚地一声闷响,擦了擦手,坐在江淮的身边:“这还用问么,我教你个诀窍,抓着人群里最弱最瘦小的那个,往死里打,只要他倒了,你就能腾出
空隙逃跑或者接着打下一个,但如果你这个打一拳那个踢一脚的话,你就是累死也冲不出去。”
言犹在耳,江淮心中豁然开朗,拳风一转,对着刚才率先袭击自己不成的人轰了过去。
那人一惊,立马屈起双手抵挡江淮。
拳肘相撞,那人踉跄后退,江淮却不惧身后几人的追击,又是一拳,仿佛街头斗殴的流氓一般,重重捣在那人的鼻梁上。
一人倒地,江淮顿时觉得身上的压力轻了一份,如法炮制,再一次击倒一人,这才将局面重新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这不是街头斗殴吗?堂堂一个少佐竟然如此下作?”中年男人大惊,暗暗咋舌。
“宫本君你还是不如军人啊,你的手下只能算是民间的保镖罢了,真正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根本不顾什么章法规则,
战场的规则就只有生死,只要能活下来,什么卑劣的手段都无所谓,死人的手段再如何光明,也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武藤生眉开眼笑,语气却十分认真地和宫本讲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