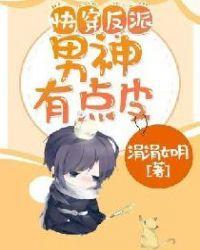墨澜小说>泊秦淮(原名银瓶春) > 南柯记二(第3页)
南柯记二(第3页)
他启开它,先闯入眼中的倒不是那粉色的小药丸,而是那盒儿内芯上画着的一幅画。
银瓶蒙眬中瞥见后,涨得面皮儿都要破了,伸手就要去抢,却被裴容廷轻而易举地躲过了。他合上盒盖,看向了银瓶,心里有了个影儿,便不由得沉了脸,肃然道:“你同我老实交代,你怎的把自己作践成这样?”
“我……大人……”银瓶倚着他宽阔而坚硬的胸膛,他的男子气简直要从四面八方将她淹没,每一次的呼吸起伏都能引得她浑身轻轻颤抖。她有心寻个妥帖的借口,可人赃俱获,再加之她如今这有赛似没有的脑子,只有实话实说的份儿。
她嗫嚅了两声,终于和着啜泣吐露了出来。
“大人当我想吃它吗!可大人天生……天生伟岸,奴只怕承受不了。”银瓶也并不算爱哭的人,但许是那药吃得太多了,又或许是情绪无处宣泄,索性化作眼泪,越发抱着裴容廷的手臂,把心事全呜咽了出来,还连着给他出馊主意,“我知道大人您也不舒坦,可是奴……要不大人……大人您再买一个得了,您也别卖了我,别把我推回那牢坑里头去……别的不成,笙管笛箫,海盐南调,我倒都……都会的,将来新奶奶来了,我日日陪着她解闷儿——”
裴容廷听着她在怀里胡言乱语,一开始是骇然,听到半截儿又有点儿忍俊不禁,可唇角还没弯起来,心里又像被针刺了一样。
他顿了半晌,到底凝出一丝苦笑,叹了一口气,在穿廊的阑干坐了下来,把大汗淋漓的银瓶打横抱在怀里,抽出自己的汗巾给她沾沾额头,看她还在喃喃,知道还糊涂着,索性拨了拨她的脸颊,咬着牙笑道:“好傻子,卖了你?你倒残忍,叫我剖心剜肚地卖了自己的心肝儿!”
银瓶当然是无知无觉。
她嘴里不识闲,说到口干舌燥,渐渐也没了声音,只是那团火终于从里到外烧到肌肤上。她的头昏昏沉沉,纱衣摩挲着皮肤,也像是刀刮一样。她摸索着就要去解领子的盘扣。裴容廷愣了愣,忙别过了目光,抱着她起身,往东厢房自己的卧房去了。他一壁护着她的领子,不叫她继续解,一壁吩咐人打水。进了屋,他才把她放到床上,看着她在床上扭股糖似的折腾,心道光靠她自己发散不是个办法,他想了想,又出了屋门,吩咐厨房煮浓茶解酒。
然而等他走回来,毫无预备地看见了月下的银瓶。
是了,月光和银瓶,还有那堆在地上的衣裳。
她竟已经抱着被子合上了眼。那被子缠在她身上,也不知怎的就这么合分寸,犹抱琵琶似的掩住了身子。一绺青丝挣脱开了,长长的,拖在枕上垂了下来,垂在地上。
裴容廷怔了怔,猛然顿住了脚步,皂靴踏在那地衣的月影上,半天挪不开步子。他是久惯牢成,早已练就沉静威仪的人,甚少有这样心虚的时候,他下意识往别处瞧,忽见那回文雕花的合和窗仍开着半扇,立即走过去关上了它。
吱呀一声,寂寂的声响,窗子合上,也挡住了那仅有的暗淡银光。满室黑暗,他徐徐舒出一口气,却又听见身后银瓶细声的呓语。她是给药住了,早没了克制,身上怎么不好,就怎么表示出声来。
银瓶在床帐子里的声音,一声儿高一声儿低,百转千回,直顺着裴容廷的脊梁骨往上走。
他背对床站着,强抑着心智,那股子销魂仍能找着缝儿漫进他的心窝子里。战场上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庙堂间更是杀人不见血的险恶风波,他什么没见过。天底下也就她一个人,单是那两声叫唤,就能把他扰得魂不守舍。
可是……不成的。
他没忍住,回头又瞧了一眼,夏月里帐子轻薄,重重叠叠仍能瞧见那一抹细小的白——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太瘦了些。况且对她而言,昨日他俩才算是初会,人生面不熟,她又显而易见地怕他,他大大咧咧地便将她吃拆入腹,实在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裴容廷把手搭在窗棂上,皱了皱眉,很快转回了身,也不叫人,自己点了灯,开柜子另取出一条绿绸闪缎锦被。他回到床边,先把那棉被罩在她身上,隔着被子抱她起来,一只手托着她,一只手去兜被子,把人往里头卷了个卷儿。
就在这时,有小厮来了竹帘前禀报,说已经炖好了苦茶。
他于是要哄银瓶起来,低头叫了两句,只听见怀中两声游丝一样的娇哼回应。他只当她在说话,听不清,便低下了头,附耳问了一句“什么?”,静了半晌,方又听见一声娇滴滴、滴滴娇的“大人”。
“奴已……唔,奴已好了许多,大人若要尽兴,只管……唔,奴是不打紧的。”
银瓶眉间微蹙,合着眼睛细声细语,那呵气如羽毛般拂在他耳根子底下。
裴容廷怔了怔,随即猛然一个激荡,洪水快要决堤似的,让他咬紧了牙。
“我知道,你一定恨我,”他垂着眼,似笑非笑,“恨我当年弄丢了你,恨我四处寻你不着,叫你白吃了这许多年的苦,更恨裴家——”然而他顿住了,蓦地皱了眉,也没再说下去,只转而淡淡道,“以至于如今你这样钝刀子割肉地凌迟我,是不是?”
他在银瓶的脸上掐了一把,又把她轻轻放回榻上,提袍出门,唤了丫头来服侍。自己则踱到外间书房,在案前的一张藤丝甸矮东坡椅上坐着。那书案上堆着许多送礼的尺头书帕,他随手挑了一本《十三经注疏》,强忍着心烦意乱,剔灯看进了书。
也不知几更天了,终于有丫头来禀报,银瓶吃了浓茶,又吃了煎姜汤,服了安神药,已经睡下了。
裴容廷缓了一口气,这才叫人收拾家伙,在书房的一张大理石金缕凉床上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