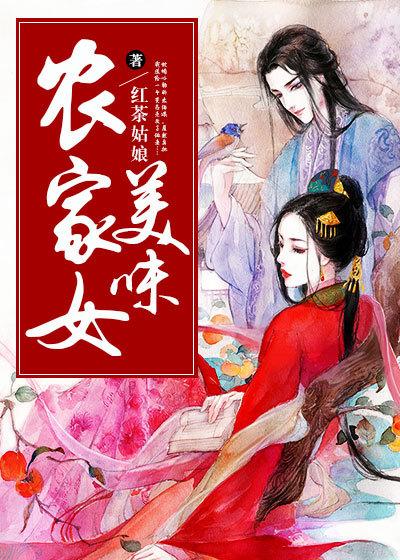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他的性别有点怪[快穿] > 俏夫郎十五(第2页)
俏夫郎十五(第2页)
这是对待心仪之人的态度吗?
怎么不夸夸他?
他与手下的官吏忙碌到大半夜,就为了今日能抽出空来见见盛如宝,这么一见,不仅没得到娇哥儿的欢喜接待,还……
他凉凉地问:“你嘴怎么肿了?”
“啊……?”盛如宝面露尴尬。
柳堰丛鹰隼般的目光下移,瞥见他衣领处若隐若现的红痕,他用玩笑的口吻问:“谢芒亲的?还是……你还有其他人?”他说出了本不该说的刻薄的话。
但他太酸了,心中像在酿着一缸醋,酸蚀得一向自持为傲的冷静都只剩下了残渣。
来时路上满心的憧憬与紧张都化为了猜忌和愤怒,脑海中闪过第一次见到谢芒时他做的事,以及前几天盛如宝在车厢上梦中的呓语。
盛如宝懵了一下,软声道:“没有其他人。”
柳堰丛逼问:“他不是不行吗?还是……你在骗我?”为什么说着心悦他,却还让其他男人碰他?
盛如宝头大,一个谎言就要用无数的谎言去圆,柳堰丛此刻的态度,不知道还以为他才是疑心妻子出轨的正牌丈夫,盛如宝硬着头皮道:“他就喜欢这样。”然后垂眸故作伤心道,“你要是嫌弃,就走吧,只怪我管不住自己的心,不配喜欢上你。”
玄色:……不得了不得了。
果然,柳堰丛一听,顿时不敢再说,被盛如宝这表白的话哄得晕头转向,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有些……”他顿住,转移了话题,“你先吃饭,等下别冷了。”
——他只是有些患得患失了。柳堰丛以前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这种情绪会出现在他的身上。
盛如宝暗自松了口气,以为这事就揭过去了,直到他放下筷子,就听柳堰丛幽幽开口:“他除了弄你一身涎水还能做什么?”
盛如宝徐徐脸红……
他对玄色抱怨:【他怎么这样说话啊!】
柳堰丛收拾好食盒,与盛如宝对立而坐,相顾无言,戳破了窗户纸以后,他们的相处反倒局促尴尬了起来。
柳堰丛反思自己的口不择言,盛如宝曾说喜他的“谈吐不俗”,可自打他们说开了以后,他却屡次说些粗俗话。
他像是个色令智昏的人,他的城府与稳重在这个娇哥儿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叫他总在无知无觉中乱了分寸,变得笨嘴拙舌。
他有些犹豫得开口:“他虽……不能人道,但对你尚可,你当真对他毫无感情?”
原主是经常贬损谢芒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盛如宝挑了一段读:“他木讷无趣,言行粗鲁,还不解风情,我实难喜欢他。只怪我命薄,被发卖前读过几本书,与他们说不到一块去,不然,也就如死灰般过了余生。”盛如宝念着有点不开心了,原主居然这样说谢芒!
柳堰丛听了却并未感到开心,他那么轻率的就说喜欢自己,喜欢的也不过只是些表面、片面的东西,若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也不如他想的那般,亦或者他见到了更好的人,是否又会琵琶别抱呢?
他这般貌美,只要勾勾手指,就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吧,就如同他一样。
谢芒一介村夫,极尽可能地对他好,都未能敲开他的心门,得到的评价没一句好,而自己未来又能用什么留住他的心呢?他真的喜欢自己吗?柳堰丛开始怀疑。
柳堰丛心思百转千回,最终统统压下,反正谢芒此去要不少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盛如宝对自己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
柳堰丛没久待,与盛如宝又聊了几句,便起身离开了,他还有些公事没处理,他和盛如宝说:“明日起还同往常一般,我让车夫早晨来接你去作画。”
“好。”
画画时他们的相处模式又恢复成了往常那般,但终究是不一样了。
盛如宝正低着头在画纸上粗略的画着地形,他偶尔抬头看看,再低下头去,纤长的眼睫随着他的动作也时起时落,好似停靠在他眼睛上的一只蝴蝶,他眨眼时,抖动的睫毛仿若蝴蝶震颤的蝶翼。
柳堰丛看的失神,有那么一刻,他差点低头吻了上去。
自打他们说开了以后,盛如宝反倒不似之前那般会刻意与他有些肢体接触,柳堰丛心里似有猫挠,痒的不行,他烦闷的想着:这是欲擒故纵吗?如果是,那“纵”的已经够久了;又或者是他得到后就对他失去兴致了?想到这里,他感到不安。
他生怕这“两情相悦”只是一场梦,只是自己的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