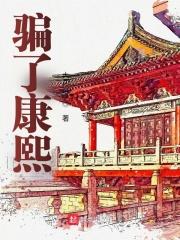墨澜小说>你你你你不识好歹 > 9(第2页)
9(第2页)
“羊毛毡?那是什么?”
齐孝川穿针引线,眉头越皱越深,只巴望他们马上结束对话。
骆安娣说:“就是用针戳刺羊毛,直到毡化,塑形成工艺品的形状。”
“什么?还能这样?羊毛不会痛吗?”
“哈哈哈,应该不会吧。希望不会。”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秘书的声音听起来尤为聒噪刺耳。
齐孝川突然敲击桌面。
茶杯发出清脆的哆嗦声,他们也齐刷刷看过来。他说:“能安静点吗?”
骆安娣还是笑着,一点没乱阵脚,微微颔首道:“当然。非常抱歉,影响到你了。需要我帮忙看看吗?”
出乎意料,齐孝川丝毫没有藏拙,直截了当递给她,伸手在示意图上滑动,示意道:“这里有点……”
“嗯嗯,”骆安娣俯下身,帮忙补充线条,与此同时,柔软的发尾落下来,像蜻蜓透明的翅膀般无声无息地摇曳,“让我来吧。”
集中精神的时候,她习惯稍稍抿一下嘴唇,轻微而迅速得不易察觉,就是这么平淡的动作。很久以前,齐孝川似乎还针对这个抱怨过:“你是吹管乐器的吗?”她轻而易举就弄好,灵巧得像是双手生来就是为了做这个。倾斜视线时,他正注视着她的太阳穴,本该不被觉察的窥视顿时败露,他躲避了眼神,她却反倒聚精会神看过来。
“客人你,”骆安娣说,“长着一张不幸福的脸啊。”
诅咒,又是诅咒,而且还是威力非同小可的那一种。齐孝川猝不及防:“什么?”
刚刚出去接电话的秘书小跑回来,及时打断这一刻的僵局:“我先回去了。我女朋友那里出了点事。”
“咦?”骆安娣也被转移关注,拿起座位上的公文包递过去,“怎么了?慢一点,请不要落下东西。需要帮忙叫出租车吗?”
他急匆匆地回复,走之前还把杯中的红茶一饮而尽:“不用了。”
齐孝川也站起身:“发生什么事了?”
“她妈妈怀孕了。”
“什么?”
“就是她妈妈又怀孕了啊,我女朋友的妈妈。她气得半死好像,现在正一哭二闹三上吊呢,”秘书边往外走边说,“五十多岁了的爸爸妈妈还生二胎什么的——”
被留在原地的齐孝川和骆安娣没有面面相觑,却也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
之后还说了些什么呢?齐孝川不记得了,他只知道骆安娣回去了柜台后。然后他就继续绣着,绣着,绣着素昧平生甚至连一面也没见过的女人的脸。那不是一个小工程,但他的确做得很投入,灯亮度细微的改变都没注意到,直到茶杯在他面前被填满。因为长时间盯着针线,连视野都模糊了,抬起头,他一时间没看清她的脸。骆安娣说:“也要注意休息喔。”
她是真的一点都没变。
即便在分别时也毫无烦恼般微笑的骆安娣,对待任何人都不可能放任不管的骆安娣,这么多年无影无踪的骆安娣。
不费力气地判断出按这进度完成不了,齐孝川将未完成的手工艺品放回原位,随即起身去结账。
骆安娣熟稔地使用收款机。她没有涂指甲油,手指边也没有任何死皮,纤细的指腹突出了关节,垂着脸,因此睫毛也格外分明。
齐孝川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思绪却飞驰回到许多年前。
骆安娣忽然朝他伸出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