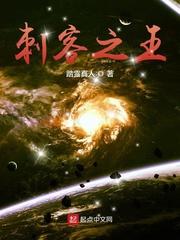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穿成吕布女儿的我太难了[三国] > 150 逐鹿天下05 安排上了(第2页)
150 逐鹿天下05 安排上了(第2页)
陶谦直勾勾地盯着糜竺,不吭声。
“曹孟德擅长用兵,诡变多端,他主动撤退,为防止偷袭,定然会布置精锐断后,”糜竺认真解释道,“我登楼观望,见曹军阵型整肃,兵马有序,无半点仓皇之态,显然准备充足。我们若于此刻出兵,便是正中他的下怀。”
“……子仲言之有理。”陶谦虽不甘心,却也没有固执地坚持,而是听取了劝诫。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道:“我思来想去,还是应该派个人往取虑走一趟。”
吕昭逼退曹昂后,一直不远不近地缀在他们后方,直至跟陈应汇合,进入取虑城。
她留在取虑不走,固然能震慑蠢蠢欲动的曹兵,但也能趁机拿下防备空虚的下邳国,进而挥兵直指东海郡啊,她是有这个能力的!
人心幽微难测,与其互相猜忌,使得好好一件美事以狼藉的结局收场,倒不如提前把话说清楚。
明白陶谦在想什么的糜竺毛遂自荐:“属下愿为使君分忧。”
经此一役,陶谦的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必须得留下陈登协助他主持大局。
陶谦招招手,唤糜竺上前来,他丢了拐杖,用力握住糜竺的手晃了晃,正色道:“那便交给你了。”
*
确认荀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后,吕昭又去安置伤兵的院落转了一圈,亲自检查每位伤员的恢复情况。
“您这药真是神了。”被陈应派来协助治疗的医师捧着吕昭交给他的小瓷瓶赞不绝口,“刘都伯伤得那样重,小人差点儿以为没救了,结果用了您给的药,血一下子就止住了,第二天就退烧了。”
“此药是华神医根据我家祖传的秘药研究改进而成,专治刀伤。”吕昭解释道,“你若是想要,等下我给你抄一份方子,照着配就是。”
“这、这如何使得!”医师先是一愣,紧接着慌忙推辞,话说得结结巴巴,“君、君侯明鉴!小、小人绝无觊觎神药之心!”
“怕什么?我没别的意思。”吕昭失笑,“药本来就是给人用的,如果不能治病救人,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我将药交给华神医时也是这样对他说的。”
医师小心翼翼地偷觑吕昭的神色,确定她是认真的,没有讽刺也没在说笑,瞬间激动得嘴唇都有点哆嗦。他对着吕昭用力鞠了一躬,语无伦次道:“君侯高风义节,小人铭感五内!请您放一百个心,小人一定不会私藏药方,一定好好使用它救治更多的人!”
吕昭点点头,“如此甚好。”
两人又聊了几句,见陈应匆忙而来,医师便很有眼色地告退了。
吕昭对陈应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若非阁下慷慨相助,我这些士兵恐怕早就活不成了,此份恩情,我铭记于心,定当报答。”
陈应还穿着昨天的袍子,衣摆皱得跟腌过的梅干菜似的,原本干净俊秀的脸上冒出了一小圈胡茬,双目下方的皮肤泛起浓郁的青黑色,一看就是熬了整宿没有休息。
但他的精神很好,曹军撤退,全城的士庶死里逃生,取虑暂且保住了。
“该由我谢您才是,”陈应面对吕昭,深深地弯下腰,郑重道,“若昨夜您未至,恐怕此时取虑已被攻破,我等皆做了曹军的刀下亡魂。”
吕昭伸手去扶,陈应却躲开了,一定要行这一礼。
两人对视片刻,吕昭无奈地轻叹一声,没再推辞。
对吕昭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后,陈应问道:“不知君侯接下来有何打算?”
如果是平时,陈应绝对说不出如此直白的话,定要绕上个山路十八弯,再配合眼神暗示一番。但目前情况紧急,曹军虽然撤退,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根本没有给他留下含蓄的余地。
“本想尽快告辞,但他们的伤势着实凶险,不宜挪动,”吕昭指了指病房的方向,诚恳道,“还望阁下能允许我再多待些时日。”
此话正合了陈应的意,他欣然应允:“这是自然,您且安心住着,有什么需要的,遣人去同管家说一声便好,千万别客气。”
吕昭微微一笑,“那便有劳了。”
了却一桩心事后,陈应的心情变好了一点点,但想到接下来要办的事,他的心情又变得沉重了。
吕昭察言观色,大概猜到了陈应要去做什么。她道:“气温渐热,将军谨防大疫。”
陈应怔了片刻,原本挺直的脊背忽然就垮了几分,“不瞒君侯,我正要去。”
吕昭轻声问:“可否与阁下同行?”
“……荣幸之至。”陈应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今天的他都这样了,已经没有形象可言了——举起袖子,胡乱擦了把脸,袖口沾上一抹可疑的水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