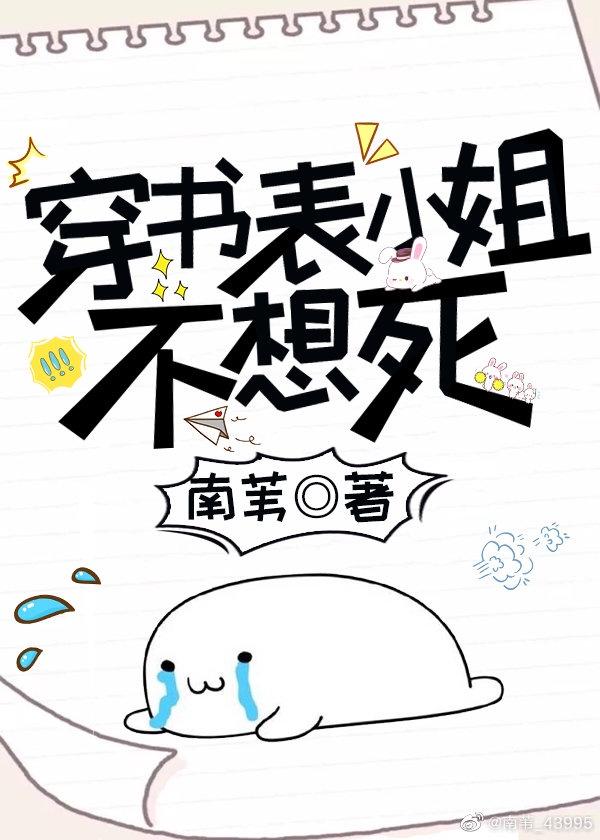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千金令:嫡欢 > 第342章 幸灾乐祸二更(第2页)
第342章 幸灾乐祸二更(第2页)
喝完了茶,云澄也就照例回了自己那边。
祁文晏则是又去了书房,继续处理他的公务。
此时的长宁侯府之内,虽然管玉生呵斥了门房的下人,不准他们乱传话,但是祁正钰鲜有的失态之举惊动了余氏。
老太太闷不吭声伏低做小这么久,就等着抓老头子的把柄,发现这样的反常和漏洞,当即就派了谷妈妈去打听。
谷妈妈对老头子十分忌惮,可是她端着余氏的饭碗,又不能不听吩咐,就好说歹说的劝着,当天夜里没敢轻举妄动,一直熬到次日祁正钰出门之后她便想方设法去打听。
使了些银子,又软硬兼施……
门房的人又不是谁的心腹,最终还是被她撬开了嘴巴。
“昨儿个三爷回来的事老太太您的知道的,说是走的时候刚要迎着侯爷回府,说了些过头话,当场把侯爷激怒了。”谷妈妈遣散屋子里的丫鬟婆子,独自对着余氏禀报。
余氏只会比祁正钰更不待见甚至是更恨祁文晏的存在,尤其昨天又听说祁文晏将要攀上皇亲的消息,就更是又气又恨又无奈。
“当初我就说不让把那野种领进门,是他偏不听。”余氏现在最乐意见的还是老头子倒霉吃瘪,便是幸灾乐祸起来,“现在好了,养出一条白眼狼,他这是活该。若是真叫那小子攀上了皇亲,以后他祁正钰怕不是也得在那小子面前点头哈腰的侍奉了?”
谷妈妈心道,如果老头子直不起腰来,您在三爷面前就更直不起腰了,夫妻俩还是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日子过成自家家主和主母这样的,也属少见。
不过这些话,她自然是不敢说也不敢提的,就低眉顺眼的从旁站着。
余氏却兴致很高,就想知道老头子的丑事,继续刨根问底:“你是说那野种与他当面呛声了?都说什么了?”
老头子是个有城府的人,当时大房那边和他当面叫板,他也没气成今天这样,回来狠命的砸东西泄愤。
谷妈妈面有难色,迟疑了一会儿才小声道:“就是话赶话……都说的气话,侯爷见面就说了三爷的不是,三爷回嘴,说……说他的确是记了侯爷的仇,恨不能要了侯爷的命之类的过激言语。”
余氏大惊失色,好半天才不可思议的呢喃了一句:“他这是疯了不成?”
这种话是可以说的吗?
若是传出去,被言官参上一本,祁文晏怕是连官都没的做的。
余氏现在也恨祁正钰,恨到巴不得对方早早蹬腿儿,可这想法再强烈,也一直都只是在心里嘀咕罢了。
祁文晏这事儿该是给她冲击不小,她坐在那里,好半天都跟入定了一般,没再有任何反应。
门房那里杨氏安插在那的两个心腹婆子,昨日本来是一个不当职,一个临时有事回了趟家,就刚好错过了祁正钰与祁文晏之间的冲突。
也是凑巧,谷妈妈去打探消息露了马脚,这会儿门房的婆子吴妈妈就第一时间赶来了栖霞园。
杨氏今日一早去了杨青云府上,因为长汀镇老家那边送了好些年货过来,杨青云每日早睡晚归的顾不上处理,就捎信过来求了杨氏过去代他处理。
所以,那婆子就直接找来了春雨斋。
彼时祁欢正带着祁元辰在书房写字,直接把人叫了进来。
那婆子看了眼祁元辰,便是欲言又止:“大小姐要么移步去隔壁吧。”
虽然祁元辰未必听得懂,但祁欢确实也不想让他沾染太多家里的腌臜事,于是就松开他的手自他椅子后面绕出来:“你自己先写着,姐姐有事先去处理一下,很快回来。”
祁元辰正写字写的投入,眼皮也没抬。
祁欢领着那婆子回了隔壁的卧房,星罗跟过去站在廊下守门,顺手将房门合上。
祁欢往椅子上一坐,直接冲她抬了抬下巴:“有话就说吧。”
“今儿个一早谷妈妈鬼鬼祟祟的去寻了门房昨儿个下午和晚上当值的小厮陈九成,说是老夫人那院里有一扇门响动不对,陈九成祖上是做木匠的,就叫他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奴婢多了个心眼儿,暗中尾随敲了敲,见着他们根本没去福林苑,谷妈妈只把九成叫到隐蔽处,塞了一包东西该是银子,又说了会儿话就走了。”那婆子直接将打探来的消息和盘托出,“奴婢也怕惊动了老夫人那边,就没敢再贸然找九成,去找了昨儿与他一同当值的来顺打听。来顺是奴婢一手带出来的,也就对我说了实情,他说是昨儿个傍晚三爷出府时和侯爷在大门口争执,说了大逆不道的话。事后管玉生警告他们不准外传,但奴婢瞧着……”
人与人之间哪有绝对的秘密?只有绝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