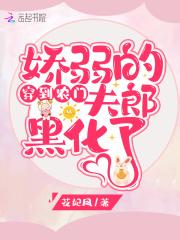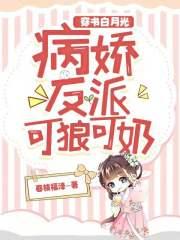墨澜小说>最美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你 > 接新生 又是一年桂子飘香时(第1页)
接新生 又是一年桂子飘香时(第1页)
银杏未黄,桂子飘香。
学校有两条林荫道最受学生欢迎。一条从学校大门口到教学楼西门,大约200米,两旁栽满银杏树,一进入冬季,落叶铺满一层又一层,满地金黄。另外一条从澡堂到宿舍大楼,大约400米,一边是桔园,一边栽满桂花树,一年四季草木清香。开学季,正是农历八月桂花飘香的季节。一些女生,在澡堂洗澡后本就一身香气,在回宿舍时一路走走停停,或驻足不前,月光清幽,香气袭人,更是富有一番情调。
四年级很多老生,都参加了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的迎新志愿活动,自愿去火车站、汽车站接来校报到的新生。甄亦凡也不例外,反正这个学期文学社刊主编职务也要辞去。学校早就放出风声,四年级校团委、学生会包括文学社团的干部一律辞职,是该腾出位子让学弟学妹们锻炼锻炼了。
日头很毒,学校迎新接待处设置在大树下,多少有些阴凉。学校提供了盒饭和矿泉水,也不至于渴和饿。参加志愿活动的老生很多,有三四十个。大家轮流接送新生,也不是很累。甄亦凡上午接送了两个新生,下午接到一个女生。“我是四年级的,名叫甄亦凡,欢迎来劳动人事学校学习”,他一把接过女孩母亲手里的皮箱自我介绍,女孩父亲没来,只有母女俩。皮箱是新的,女孩子很壮实,一身麦黄色,应该在家里日晒雨淋干过不少农活。她的母亲看起来有些苍老、憔悴,都是农村人。“我叫王晓若,自动化控制一班的”女孩子报了自己名字和班级,自动化控制是学校结合社会职业需求新开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好啊,学校新开的第一届,好多大企业要人呢”。不得不说,学校在适应社会职业变化这点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培养人才紧跟社会职业发展需求。从一开始的人事管理到劳动资源管理,再到工资管理、会计电算化、自动化控制,差不多每年都会开设一两个新专业。办学方向也从为党政机关培养政工干部逐渐转到为企业培养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工作。
甄亦凡带母女俩等校车,又亲自带着她们找到班主任报名后送到寝室才离开。目睹王晓若的母亲给孩子铺床的背影和两鬓早生的白发,甄亦凡忽然就想到了三年前那个日子。当时的母亲也是这样,弯下腰为他铺床,直起身又为他挂好蚊帐,尽管心有万般不舍,却也没能留下母亲陪他一夜。把父母送上火车,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背影,他的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那是他读书后第一次流泪。
而今天,在这个桂子飘香的日子里,又有多少个母亲和孩子别离,又有多少个学子暗自垂泪?这个桂子飘香的日子啊!
相比于甄亦凡他们这些志愿者的轻松惬意,身为学生会主席的王浩和校团委负责工作的副书记陈莯鸿等人自然要苦要累一些。他俩一个负责汽车站迎新点,一个负责火车站迎新点,除了登记表册还要安排统筹志愿者三餐和饮水,以及新生和家长迎来送往。从天亮一直忙到月亮升起才收工,一整天都只能在热浪灼人的水泥广场上奔来往去,一身大汗湿透了衣服,也没空闲休息一下。
第二天上午,甄亦凡又接到了一对父子。交谈中得知来自怀化山区农村,因为父亲要赶火车连夜回家,等不及校车,甄亦凡只好带他们去坐14路公交车。他们父子两人坐在前面,甄亦凡坐在后面,看着这个有些佝偻的背影,他恍惚间看到了自己身在乡下的父亲。
2007年,离他的父亲送他去学校16年后,甄亦凡又带着父亲坐了一次14路公交车。那一天,在得知病情最终确诊后,还不到60岁的父亲,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只是提出来带他去黄花机场看看飞机。这一辈子,他还没有近距离感受过真正的飞机。强忍住内心的悲痛,甄亦凡带着父亲从省肿瘤医院坐车到公交站,转乘14路公交去黄花机场。车子一路疾行,当路过学校看到窗外“劳动人事学校”的校牌时,他一路忍住的泪水终于盈眶而出。看着前面因病瘦了一圈的父亲,他想起了1991年的那个夏日,想起了父亲和母亲送自己到学校的情景。那一天,走得也是这条路,从学校返回火车站的14路公交车上,他也是这样,坐在后面默默地注视着父亲因为劳累而佝偻的背影。
2009年清明,他写下了那篇散文《怀念父亲》。
怀念父亲
--写在父亲去世一周年纪念日
几次提起笔又放下,回忆父亲,犹如面对湘西老家莽莽群山,无崇伟之处却又绵延无边,满腔情,却叹无处着墨。
—题记
去年的今日,父亲走了,去了那个遥远的地方。
不到60岁的父亲,走在意料之中却又那么得突然。六月六,这个土家民族最热闹的节日里,劳累一生的父亲终于歇了下来,永远地歇息了。那天的日头很毒,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呵!而今天,却下起了雨,淅淅沥沥,雨丝绵绵长长,一如坟前的我对父亲的思念。
父亲其实很普通,对我们四个孩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爱。或许,他只是尽着一个为人之父的本分,就如家乡随处可见的大山一样,贫瘠的土地,产不出丰盛的大麦细粮,却坚韧地生长着苞米、土豆和番薯等杂粮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山野水果,把一代又一代土家人喂养的壮壮实实。
打从记事起,就很少在家中见到父亲,只记得他匆匆忙忙、好像永远不知疲倦的背影。上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父亲象松了绑似的,整日里扑在田里地里,不到两年就让家里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润。后来我们四弟兄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世上,老房子挤不下了,父亲一有空就到河里挑砂石、到砖窑挑砖瓦。满天星斗的夏夜里,梦中被尿憋醒的我经常会遇到父亲,他有时正挑着一担砂石远远走来,“嘿呼嘿呼”的喘气声在安静的夜里特别大;有时正弓着腰小心翼翼地码着火砖或青瓦,生怕吵醒熟睡的我们。日晒雨淋、披星戴月,晒黑了皮肤,压弯了脊背。墙角里挑烂的竹撮箕和烂草鞋也越堆越高,也记不清是两年还是三年抑或是更久,五间大砖房硬是他一肩一肩地挑了起来,让我们一家子有了一个舒适温暖的窝。
母亲一字不识,父亲也只是高小文化,他们却极为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从1982年发蒙起父亲就为我到邮局订报,《小学生拼音报》、《初中生学习报》一直陪伴着我们四弟兄的成长。那个年代里四个孩子吃喝拉撒、读书开支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母亲把日子过得极为精细,一分钱常常掰成两瓣花。父亲却经常在“六一”、“国庆”等节庆日子里一担箩筐挑着老三老四,我和老二流着鼻涕跟在后面,带我们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打折的课外书。书买回来后,我们兄弟争着、抢着打打闹闹,这时的父母亲,就像看到我们期末考试拿回大红奖状一样,笑的合不拢嘴。现在回想,那也许是我们童年全家人艰难的日子里唯一的亮色。
“老实人占不到便宜也吃不了大亏”,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有几次收摊后对账发现多收了事主的钱,他和母亲硬是连夜赶几里山路把钱退给了人家,不过这也为家里的小生意留住了更多的顾客。别人家有大务小事,父亲总是不请自到搭把手,因此在村里人缘极好,大家都很相信他。父亲不是村干部,村民却要他管着集体的钱,一管就是十多年,就是病倒在床上了,也没人来找他清账。倒是他自己觉得时日不多了,要我请来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清清白白地交了账。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父亲也好烟酒,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劳累一天后灌二两包谷烧,卷一杯纸烟,捧一本《薛刚反唐》之类的通俗演义,蹲在那盏昏暗的灯泡下,往往一看就是半夜。第二天天不亮又到山里忙活去了,也不知他哪来的精力。
开头几年,父亲一年四季忙在田间地角,母亲在街头巷尾做些小本生意,日子还过得去。后来我和老二相继读了中专,老三老四上了高中初中,家中的日子就益发的艰难了。97年,老二财专毕业遇上分配体制改革没有分配到工作,读书跳出农门的念想断了,乡邻们的嘲讽也扑面而来“书读的再狠再多又有卵用,钱花光了最后还不是落得一个打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和“全民皆商”在社会上泛滥的年代,村里跟老三、老四同龄的孩子早就做生意或外出打工去了。记忆深处,一家人好像由天上掉到了地下,陷入黑暗和彷徨之中,那是一个多么漫长、多么难过的暑假啊!“就是打工,读了书也要强些”,开学前夕,父亲把老三和老四送上去学校的车,他选择了坚持。我也推迟成家,一家人拉扯着送他们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历经几年的艰难,家中的日子眼看着朝好的方向转变,我由乡里调进县城机关,三个兄弟打拼几年也逐渐在外面站稳了脚跟,却万万没想到……
当医生拿着CT结果告诉我父亲只有几个月了,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时,我一下子懵了。最艰难的处境过去了,好日子才刚刚冒个头!我强忍悲痛,叫医生开了一些消炎药,安慰父亲只是肺炎而已。望着父亲如释重负地走出医院大门,我却欲哭无泪。整整一个星期,我把父亲的病情压在心底,身为长子,我不知该如何告诉年迈的母亲和在外打工的兄弟。抱着一线希望,我带父亲去了省城医院,也许那次父亲察觉了什么,要我带他去黄花机场看看,说是这辈子还没看到过真的飞机。在去机场的车上,望着父亲瘦弱的身子,回想起他当年送我到星城读书的情景,刻意坐在后排的我泪盈满眶。
孩子们筹措了医药费,父亲却拒绝治疗,从省肿瘤医院逃了回来。他有他的想法,我刚在县城买房子还欠着一大笔账,三个兄弟也没成家,他还听人讲就是治疗效果好也只能拖个两三年的。最后我们没办法了只好威胁他不治疗就放弃手中的工作回家陪着他。或许为了安孩子们的心,他拿着省医院的治疗方案,选择去了吉首医院,只为了医疗费用便宜些。住院化疗时,我请过两次假去陪他几天,被他赶了回来,母亲陪他他也不让,独自一人打完针就到吉首市里四处转转。在外打工的兄弟也只能请三五天的假来看看他,心里再急却又不敢辞工,医院要的是钱。我们四弟兄都一门心思地想着挣一分是一分,用钱把父亲保住一天是一天,更期望着哪一天奇迹会降临。现在回想,在选择打工挣钱救治他和放弃手中工作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日子的选择中,我们或许错了。也许更应该陪他走完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
接受治疗后,父亲乐观的本性露了出来。每次从医院化疗回家后,他四处串门,打牌聊天吹牛皮,还安慰母亲说是医院搞错哒。也许正是这份乐观的心态,让他从医生宣布的三个月活到了一年多。2008年春节,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冰冻灾害,三个兄弟辗转半个多月从浙江、深圳赶了回来。春节期间,我们几弟兄极力逗着父亲,父亲也尽力装的若无其事。春节过后,老三老四陪着,父亲坐飞机去深圳玩了一个多星期,照了许多像,每张相片都是笑呵呵的,像个贪玩的孩子。
父亲生病几个月后,我家女儿生了,是父亲第一个孙女,我想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他今生唯一能看到的小孙子了。孩子出生后,他几次到我家里来,我也几次把孩子抱回乡里老家。每次把孩子递给他,他却不接,只隔老远看着,只因为他是个病人,生怕自己的不干净对小孩子不好。父亲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那份爷爷对孙女的爱怜,也只有我这个做儿子的,看得懂!
父亲一直顽强地和病疼做着斗争,哪怕倒床不起了,每餐都霸蛮的吃一碗稀饭,直至去世都没打一针杜冷丁。每次陪父亲到半夜过,从来没听见他喊声痛,可第二天早上一赶到单位母亲电话就追来了,讲父亲痛的受不了。那段时间,刚调进城工作上特别忙,家里照顾孩子乡下陪伴父亲两头跑也很累,有时免不了埋怨母亲不经事。现在才明白,肯定是父亲怕我夜里太劳累才强忍着痛疼没出声,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坚韧呵!曾记得有几次早上醒来为父亲擦去满头的大汗,现在回想,这肯定是他强忍住疼痛没喊出声的缘故。他的顽强与坚韧不但导致了医生对他病情的误判,也让孩子们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他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守候在身边。老三已辞工,一心赶回来伺候他的,可没想到他走的那么突然!头天晚上,母亲还喂了他半碗稀饭,我也一夜陪着他,早上出门也没听见他喊声疼啊。
还是在星城读书时,因为想念父亲而写过一首小诗《犁与父亲》“岁月老去犁铧锈了父亲亦如堂屋那张老犁一头驻在地上一头仍旧翘首远望……”而今,犁耙高挂在堂屋,而父亲已远去,只留下那张遗照,在堂屋供桌上,照片上的父亲象生前一样,慈祥的望着我们。
草于己丑年夏
刚才还是阳光毒辣的,教室里极其闷热,却不料一下子外面的天忽然就暗了下来,紧随着一阵阵雷声自遥远的天际,一步步逼近,直到头顶,轰然炸响。起风了,树叶在空中乱舞,依稀有雨飘过窗户,落在手上,一丝凉爽,瞬间传遍全身。
风逐渐变大,雷声依旧,细雨依飘。
慢慢地,飘飞的雨丝凝成细线,窗户上的玻璃,也开始一滴滴地往下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