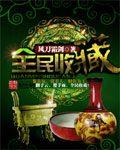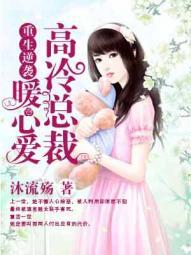墨澜小说>清冷权臣为妖妃折节 > 故人(第2页)
故人(第2页)
渭河,离镐京已有千里之远,李瀛平复呼吸,接过青俪递来的清水,小口小口地呷着。
“现下船上大半是咱们的人,沈主薄说,若是娘娘近日醒了,便在下一个渡口下船,先行离去,等他主持完丧仪,解决手尾再来与娘娘相会。”青俪低声道。
眼下在渭河,下一个渡口……便是潼关,李瀛在心底描摹着从前看书时看过的大晟舆图,当即道:“那我们便在潼关下船……”
还不等她把话说完,眼前骤然一黑,浑身发软,耳边只余青俪惊慌的声音:“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再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方床榻,穹顶用木槅板架起,身下铺着茵席,松软温暖,身上盖着薄薄的绣花被衾。
侧头看向帐外,外面光线更加昏暗,只余一盏油灯轻轻晃动,借着烛光,依稀能看见床榻边缘趴着个乌黑的脑袋,一根朴素的银钗梳着民间妇人常见的云髻,是青俪。
她这般打扮,倒让她有些陌生。
李瀛试着开口,骤然发觉喉咙有些嘶哑,她忍不住咳嗽几句,压抑的咳嗽声在船舱内响起,青俪睁开眼,声音里满是后怕:
“娘娘,您方才突然昏过去了,这船上缺医少药,又不便惊动旁人。我便取了那抹沈主薄之前送来的丹药,给您服下了。”
李瀛点了点头,发觉身体确实舒服许多,她心中清楚,青俪所言不假。此程若是没有先前沈谙之送来的丹药,以她这幅身子,只怕捱不到潼关便要病倒了,欺君之罪一旦被发觉,届时不单是此行功亏一篑,还会牵连他们的九族。
经幢飘动,脚步声由高及低,似是有人沿着木梯而下。
青俪连忙掩好纱幔,急匆匆挡住隔板,将李瀛遮得严严实实的,再回头,看清来人,神色骤然一松。
来人赫然是沈谙之,玉冠束发,穿着皂服,显然是刚刚沐浴过,身上还透着皂荚的清香,手中托着一只小匣子。
“来时在下为了以备不测,夤夜钻研医理,买药材制了丹药,娘娘看看,可有用得上的?”沈谙之压低声音,隔着一道木板和帐内的李瀛说话,同时将匣子递给青俪。
“多谢你了,此行若不是有你,只怕……”李瀛又问道:“那枚太医院送来的丹药,可是你命人打点的?”
沈谙之犹豫一瞬,从船舱内的氛围里察觉到一丝端倪,面不改色地答道:“这是在下分内之事,娘娘不必再提。”
无论给娘娘送药的人是谁,离了镐京,他们此生都不会再有见面之机,把这个恩情给他,又有何妨?
话音甫落,船舱内安静了一刹,随后李瀛的声音继续响起:“沈郎,多亏有你。”
她改了口,短短二字,沈谙之几乎欣喜若狂,高悬在宫墙上的明月骤然落入他怀中,岂能不让人失去理智。
沈谙之竭力平复心情,声音里还带着几分激动:“娘娘……瀛娘,等御船到了潼关,我便安排你们二人下船,等我解决完丧仪仪,回到镐京辞了官,便与你隐逸江湖,此后逍遥自在。”
说到激动处,他的声音都微微颤动起来,一口气说完,等了顷刻,帐内终于传出李瀛的声音:“好。”
仅仅只有一个字,却让沈谙之喜悦得不能自己,恨不得立即在这逼仄船舱内痛饮一壶,亦或者登上甲板,迎着江风放声高歌一曲。
人生快意,不过如此。
等到沈谙之离开,青俪放下挡板,纱幔中,李瀛的面容如同隔雾看花,让她看不真切,“娘娘,当真要和那位沈……在一起?”
李瀛轻轻看她一眼,那双微弯的眼角带着她看不懂的意味:“那是自然。天底下,还有比沈郎更好的郎君么?”
一语落毕,头顶上骤然响起一声细响,那是通向上层的槅板合上的动静。
就在刚才,沈谙之,还没有离开。这个念头让青俪面色微变,她抽出银钗,隐在发髻中那一端锋利光亮,显然是早有准备。
李瀛接过银钗,让青俪转向前面,将枕骨露在她这一面,专心地给她盘了一道云髻。
……
浪涛声中,潼关到了。
在沈谙之的掩护下,李瀛悄悄下了御船,青俪紧缀其后,二人踏上码头,混入熙攘的人群。
李瀛接过青俪手中的皂纱,戴在头上,扎好系带,严严实实地掩住面容,骤然发觉远处似乎有一道视线盯着她,下意识抬眸望过去,隔着人群,措不及防地撞进一人漆黑深邃的眸底。
……他怎么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