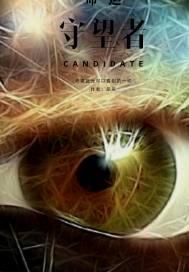墨澜小说>重生后要当富一代 > 藏宝洞(第1页)
藏宝洞(第1页)
"您看啊,"李大牛越说越来劲,"咱在汪边搭几间草房,弄个理发部。外村人来了,花两毛钱就能在青沙汪里挖一刻钟,挖着东西归他们。要是挖累了,还能理个发、刮个脸。"
说干就干。五爷爷召集村里主事人开了个会,当天下午就派人在青沙汪北面搭了三间草房。一间摆上长条凳当理发室,一间支起大锅烧热水,还有一间摆上八仙桌,供人歇脚喝茶。
很快,理发部就正式开业了。
李大牛站在门口吆喝着,“快来啊,青沙汪挖宝,理发刮脸一条龙服务!”别说,这招还真管用,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一开始,来的大多是些老爷们,他们在青沙汪里挖得满头大汗,然后到理发室刮个脸,舒舒服服地喝上一碗茶。
拉呱的多了,就有人知道李家村有专门给女人洗澡的地方,交钱就行,还能给女人理发、烫火钳卷儿。
张翠翠自然成了理发室的"首席理发师",当然,青沙汪那边都是老爷们,想找张翠翠理发的都到李家来,反正李大牛早早出去,家里就女人孩子,来理发的妇女们也都知道。
张翠翠不但会剪头发,还会用火钳烫卷儿,很快就在十里八乡出了名。赵小田听说后,主动跑来帮忙烧水、扫地,顺便学手艺。
慢慢地,女人们也开始来了,她们对这里能烫发很感兴趣,纷纷尝试。
有一天,邻村的一个年轻姑娘来烫发,烫完后效果特别好,她高兴得合不拢嘴,还逢人就夸。
这一来,更多的女人都慕名而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五爷爷决定再扩大规模,多盖几间草房,增添一些设备,不过那得过了年的。
开业头一天,东村的王连长就带着几个小伙子来了。交了四毛钱后,王连长拿着小铲子在青沙汪里挖了半小时,还真让他挖出个铜纽扣。
"这可是好东西!"王连长举着纽扣直乐,"准是庄家老爷衣服上掉的!"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挖出锈蚀的铜钱,有人找到残缺的瓷片,最走运的是西村的一个半大孩子,竟然挖出个完好的鼻烟壶。
五爷爷坐那跟人拉呱,“哎哟,那时候,破四旧,不知道什么东西都往这里扔,这东西也不知道几辈子了。”
有人知道老事儿的也说,“可不是,那年头,坟头碑都铺了路,东西砸的砸,碎的碎,可不就填了旱汪了?我说,你们村这旱汪没人命吧?”
五爷爷的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眯起眼睛说道,"说起这个,咱们李家村的旱汪,还真没怎么出过人命。"
旁边几个老人围坐在八仙桌旁,茶碗里的热气在初春的冷空气中袅袅升起。王连长捏着刚挖出来的铜纽扣,也凑过来听。
"解放前那会儿,"五爷爷缓缓吐出一口烟,"附近几个村都有舍林,活不下去的老人孩子,就自己走进林子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烟袋锅指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山林。
赵老汉接话道,"可不是,东村的老槐树下,西村的乱葬岗,都是苦命人去的地方。"他摇摇头,"咱们李家村人少,总共才百十户,又靠着水,那时候还没有水库,可河是活水,再怎么难,捞点鱼虾也能对付。"
"要说投水的,"后屋的李大爷插嘴,"咱们村还真没有。搬迁前这几个旱汪都是牲口饮水的地方,谁舍得糟践?"
正在喝茶的老孙头突然压低声音,"我听说,庄家搬走前,往这青沙汪里扔过东西?"
五爷爷的眼神闪了闪,"那是另一回事,"他岔开话题,"你们看这鼻烟壶,做工多精细,准是大户人家的物件。"
说来也巧,老爷们谈着旱汪人命,女人们也在说着些老事儿。
女人们更爱往张翠翠的理发室跑,她手艺好,收费又便宜,村里李梅过来帮忙,很快学会了洗头、梳头,还能帮着卷发卷。
李梅是李三木的小妹,跟着嫂子赵小田过来,学了不少,给人倒水什么的也很勤快。
赵小田,学了不少,可要给人洗头,还拉不下脸,不过也经常领着云云过来,看张翠翠给人摆弄头发。
"翠翠姐,你这火钳烫得比县里还好看!"西村的姑娘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满意地掏出手绢包钱。
张翠翠笑着接过钱,顺手给姑娘别上一朵绢花,"这样更好看。"
理发室里,几个等着烫发的妇女也在小声议论。
"我婆婆说,早年间这附近闹饥荒,有人家实在养不起闺女,就。。。。。。"说话的大婶做了个推的手势,没往下说。
正在给自己洗头的人,手一抖,水溅了出来,这人是刘家洼的刘五妞,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娘总说她是"捡来的",莫非。。。。。。

![女道君[古穿今]](/img/6493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