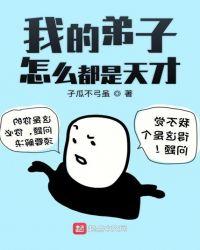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太后 > 第157章 相见(第1页)
第157章 相见(第1页)
董灵鹫在这里等了一阵子了。
潺潺的流水声淌过身侧,冥河之下,无尽的水波涌起,夹杂着破碎的生魂,停歇过后,又翻涌着退下岸堤。
她在与一位故人下棋。
这位故人的形貌,还是他此前最英俊年轻的模样,一点儿看不出病重时的苍白昏聩。他执棋的习惯也一如当年,这么久都没有改变过。
棋枰两侧的茶凉了。
在她与孟臻的对弈期间,董灵鹫明显神思不属,时常抬眼向河上长桥的另一边望去。她频频看向那里,仿佛在等什么人。
但孟臻问她在等谁,她却摇了摇头,说自己谁也没有等。
董灵鹫并不想等来那个人。
可是棋至中局,在一盏苍白灯笼的引领下,她还是等到了。
董灵鹫叹了口气,将手掩回袖中,目光远远地望着那盏灯,跟他道:“早知如此,我不如下一道旨意,不入帝陵与你合葬……我不讲究妃陵简朴,也不在意繁文缛节、后人看法,只是对他的向生之志,还抱有一丝希望。”
孟臻的手按在白子上,顿了一顿,神情有点无言以对,他抬指敲了敲棋盘,道:“我还在场呢。你能不能别这么水性杨花。”
董灵鹫道:“水性杨花?哦……你在我面前也总是三心二意、水性杨花。”
“胡说,我要是真有此想,立时就去下地狱。”他道。
“想法虽不是,身体也是了。”董灵鹫轻柔地道,“别想着让我哄你,我累了。”
孟臻:“你不是累了,你只是移情别恋了,把他埋在心里,把我就埋在土里。”
董灵鹫慢悠悠地转着手腕上的红色珊瑚珠,道:“我是移情别恋,我犯了地府的法律不成,那你叫人掐死我吧。”
孟臻穿着华贵的帝服和冠冕,极为恼火地锤了一下棋枰,弃子不下了。
董灵鹫不管他,注视着那盏白灯笼走过桥,引路的小鬼飘走之后,郑玉衡茫然的视线猛地恢复清明,像是神智重新回笼一般,他一眼见到两人下棋的地方,快步冲了上来。
岂止是冲上来,孟臻被这人扒拉到一边,明明周围这么多空地,这撬墙角的非要把他挤走,撞得棋盘一震,黑白乱纷纷,随即郑玉衡一头栽进董灵鹫怀里。
并且也把董灵鹫抱了个结实。
孟臻看得头痛欲裂,伸手捏着自己的眉心。
“檀娘——”郑玉衡刚抱住她,所有情绪一股脑儿地涌上来,根本收不住,他在别人面前一滴都不掉的眼泪,一靠近董灵鹫,就瞬息间崩塌粉碎,一败涂地,模样可怜伤心极了,“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我好想你……”
实际上,他们只分别了郑玉衡操办丧事的那一个月而已。对于董灵鹫来说,估计也就一炷香的功夫。
董灵鹫抚摸着他的背,低声:“你看,你就总不听我的话。”
郑玉衡哽咽道:“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会死掉的。”
孟臻面无表情、阴阳怪气地道:“还是你的新欢娇弱,我在地底下一个人躺几十年,也没听说过孤零零这种死法。”
董灵鹫没理他,她动作温柔地给郑玉衡擦擦眼泪:“他们几个都还好吗?”
这问的是孟诚、孟摘月等人。郑玉衡答:“虽然伤心,但不至于像我一样无能,离不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