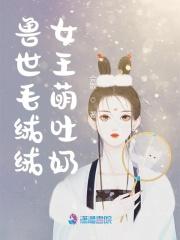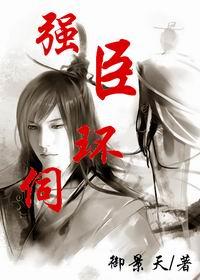墨澜小说>将笙歌 > 书楼(第1页)
书楼(第1页)
时至正午,正是用午饭的时候。
程语笙晃到孟老夫人处蹭饭,老夫人很是高兴,命人添这儿添那儿,直将圆桌摆满了才作罢。
心中记挂着孙儿新婚离京之事,老夫人怕孙媳觉得被冷落,絮叨着开解:“长歌跟在圣人身边历练,事急从权之时常有,原是单条汉一个,疯跑去哪里我也懒得管,随他了。”
说着给语笙夹菜,她满面慈爱:“现有了新妇,可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待他这次归,我便进宫求个恩旨,让他安定下来,好好和你过日子!”
程语笙吃得正香,闻言,一下子没了食欲。想起某人昨夜故意气她跟她斗嘴,她微垂嘴角,默默的应了声。
日后,若是他天天在自己面前晃,她可不愿!然……
这心思不合正道,不能叫一片好心的祖母发现。
“他正是求进的时候,得圣人赏识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孙媳只有支持,万万没有半点不平委屈的心。”
孟老夫人听她之言,赞赏她识礼大义,有女杰之风。
程语笙哪里敢受如此褒奖,忙将话重新引回老夫人身上,称与老夫人当年相比,她实是微小如尘不足为道。
话到这儿眼露仰慕,她追问老夫人当年战场上的风采,洗耳恭闻。
鹤居,侍奉的奴仆也皆上了年纪,大家知老夫人喜静,办差都是轻手轻脚。
院里夏光正盛,一株程语笙叫不出名字的花树,艳色满枝,一有风,香味就随着落花垂入院中,落座其下,极是恬静悠然。
同老夫人从饭桌上讲到了这处,她趴伏在老夫人的膝头,静静的听着她说经年往事,随着里面的旧人时喜时悲,光阴飞逝。
提及她与已逝的谢老大人曾因趣味相投,在府中共建书楼,用以存放兵书器卷。她目露怅然,时光眨眼即逝,逝人已去,楼阁蒙尘,她亦不复当年,身姿矫健了。
眼角微微泛红,她轻抚程语笙墨般的鬓发,笑道:“你爱听我说这些,想也会喜欢那书楼,若有空,你着手帮祖母打理打理,如何?”
程语笙感激应下,知道祖母是看出她喜欢,刻意成全。
起身行礼,她迫不及待的求祖母使人带她去瞧。孟老夫人无有不应,令她慢慢来,切勿太过劳累。
书楼名为藏锋,意指兵也好,器也罢,贵在藏而守和,不为争权斗狠。楼阁修缮的年头久远,中间修缮了好几回,楼名的匾额却一直没换,是谢老将军的亲笔书,每年都有子孙们亲自补漆上蜡,保持传承。
立在楼前就有一股庄肃感扑面而来,程语笙仰头眺望良久,才跟着看管书卷的老仆进了楼。
整个楼阁有七层之高,占地数亩,每层都有环绕排列的书架,延绵目极。盛景时,曾有上百仆人日日操持守护,他们不但兼收集书卷之责,亦懂得古卷修补,誊抄摘录,所以,书籍才会越来越多,远古通今。
后谢老将军离世,孟老夫人携子身在战场久不归家,谢府人丁凋零,财物吃紧,渐渐地,楼中人手裁撤,只剩几个真正爱书之人,求口吃喝,甘心留下侍书。
转眼又是十几年,萧朝战休,谢家家主归京,重振门楣,谢府从里到外修彻一新,然而终究物是人非,老侍书人相继离世,新纳的仆人大多不识字,除尘清扫或许还成,其余一概不敢奢望,每碰坏了古籍,仅剩的老仆都心疼不已。
孟老夫人曾想过亲力亲为,将书楼重新规治一番,可无奈年纪太大,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日一日的,这处慢慢不再被人经常想起,一直至今。
看楼的老奴年纪十分大了,耳背眼昏,身子佝偻,走几步就要停下,咳嗽喘息片刻。
孟老夫人多次劝他归乡,给他置宅养老安享天年,可他就是不愿,只想守在楼中老死,道这里才是他命极心安之所。老夫人不能强求,给他指派了人手帮忙,可他年老古怪,跟年幼的愣头娃娃们合不到一处,为求清净,索性将他们都赶了出去。
听闻来人是谢府新入的少夫人,又奉了老夫人的命来看顾书楼,老仆面上恭敬,心里不抱期待。
年纪还轻的小娘子,哪里能在这枯燥处受得住?都是娇主,不过一时之趣,为求暂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