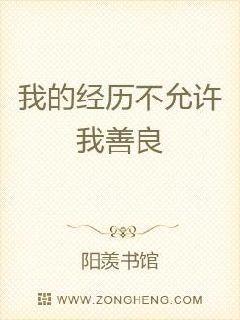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女讼师之昭雪传奇 > 来历(第2页)
来历(第2页)
因着手里拿回的是赝品,他终于按捺不住再次出手,未料到大理寺早有埋伏。
当初要是他愿听陆香茹的劝,再多忍耐些时日,恐怕就不会落得今日这番下场。
这些往日旧事听在时璎雪等人的耳里,皆是唏嘘不已,谁能料到,这件案子背后,竟然攀扯出那么些怪力乱神的传闻和秘辛。
但最关键的,便是徐子峰这口供,他虽然一直强调不是偷盗,只是取回徐家的宝物,但那“取回”的行径,他是没有否认的。
但对于强|奸一罪,他却义正言辞地矢口否认。当然,强|奸罪的罪名也比盗窃稍重些,不管是刑法上,还是在“口碑”上,“不入流”也比“下流”强些。
但时璎雪看得出来,徐子峰应当不是因为刑罚之故否认强|奸。
时璎雪眼睛一转,开口问道:“依你所言,与你有仇怨的是盛铭鑫等人,那石平呢,他是无辜的,你又为何要陷害他?”
徐子峰扯了扯嘴角:“无辜?他若是不贪心,怎会落得这个地步?”
“石平固然道德有失,但那不是你陷害他的理由。”时璎雪冷着眸子望向他说道。虽说她有些脸盲,但那画像中的犯人下巴分明挂着些胡茬子,与眼前干净秀气的徐子峰毫无关联。
在盗秦朝铁权时,徐子峰故意露脸,定然是乔装打扮过的,也就是说,他早就想好了将一切嫁祸给石平。
“石平,无辜?”徐子峰疯狂大笑,随后停顿,狠狠地盯着时璎雪,咬牙切齿道,“你可知是谁亲自掘的我徐家的组坟?正是石平他爹——石冲,但石冲好多年前便去了。所谓父债子偿,石平如何算得上无辜?”
“既然是‘父债子偿’,那你又如何证明你不是那采花大盗,不是在做那‘父债女偿’的报复行径呢?”时璎雪侧了侧头颅,意味不明地笑问。
“这……”徐子峰顿时懵住了,隔了半晌,他才找回声音,“那何观海顶多是贪财,与二十年前那桩事有何相关,我为何要报复他?更不可能对一个软弱女子下手。”
“是啊,那二十多年前的事,又与石平何干?他那时不过是八岁孩童,与你家祖坟被盗之事,又有何瓜葛?”时璎雪进而问道。
徐子峰一时语塞,他说不过时璎雪,但又不愿承认时璎雪的言辞,父债子偿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难道不是吗?石平身上既然流着石冲的血,那他就有义务洗刷石冲犯下的罪孽。
“你是讼师,舌灿莲花,我自然说不过你。”徐子峰瓮声瓮气地说道。
继续争辩也没有意义,既然徐子峰已经交代清楚案情经过,那么四桩盗窃案总算是水落石出,而石平也可借此洗脱罪名。
只是盗窃案虽了结,还有那强|奸案待破。
时璎雪回头看了眼千龄昭,只见他笔墨生花,认真撰写着徐子峰的口供,看到他那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好字,时璎雪微微咂舌,想到她自己那手龙飞凤舞的字体,多少有些自愧不如。
“大人,何小姐可有提供犯人的长相特征?”时璎雪眼神从千龄昭那指节分明的手上挪开,轻声问道。
千龄昭摇了摇头:“何小姐醒来后,情绪虽然平复了许多,但是她的嗓子也哑了,近几日恐怕都不宜开口。”
时璎雪听闻,沉吟片刻道:“或许,可以换个方法。”
让画师给徐子峰作画,而后,再从中混杂九张年龄相近的男子的画像,带去给何文心辨认。
虽然此时何文心不能张嘴复述当日情景,但是辨认犯人的能力总是有的吧。
但前提是,只要她不跟时璎雪一样脸盲。
千龄昭让廖宁去找画师按照时璎雪所言,送十副画像到何府,给何文心辨认。
“只是有一个问题,万一,徐子峰当时易容了,何小姐认不出来,又该如何?”千龄昭听闻,提出了疑惑。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徐子峰,只见他听了千龄昭的话,下意识翻了个白眼。
时璎雪打量着徐子峰的身量,拍了拍手道:“那便在画像中标明他们的身高肥瘦,这样应该更方便辨认。”容貌可以改变,但到了赤裸相呈那刻,身量体形便无可遁形了,定能叫何文心认出来。
“徐子峰,你身上可有什么胎记没有?”时璎雪抬眸问道,要是那采花大盗也跟那具“无脸男尸”一样,身上有明显的印记,那这犯人便更好找了。
徐子峰受刑都没那么生气,这是赤裸裸的侮辱,他双眼喷火道:“老子清清白白,身上干干净净!”
时璎雪有些可惜地摇了摇头:“你急什么,若你身上有明显印记,而那真正的采花大盗没有,不也能侧面给你洗清罪名吗?”真是不晓得举一反三的家伙。
虽然她说得有些道理,但这话听着咋那么不舒服呢?徐子峰没好气地哼了声。
见她一脸遗憾神色,千龄搁下笔补充道:“他身上确实没有特殊的印记。”
时璎雪惊讶回头,表情似乎在问,他怎么会知道?
“每个进入大理寺的重犯都要经过全身检查。”千龄昭不自在地咳嗽了几声,见她听了眉头微皱,千龄昭倒有些后悔告知此事了。
然而时璎雪想的却是,她哥时英杰入狱时肯定也绕不开这一个环节,又想到时英杰似有龙阳之癖,她那“为哥尴尬”的毛病又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