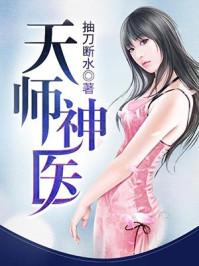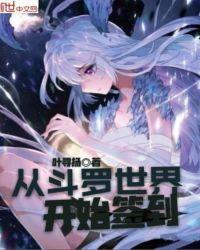墨澜小说>重生神雕:拜师李莫愁 > 第71章 全都暴露(第1页)
第71章 全都暴露(第1页)
易逐云久闻红袄军之名,那杨妙真号称“一杆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只是没有与她交过手,实在不知有几斤几两。
又念及红袄军降蒙多年,便问道:“这话从何说起?我听闻李璮之父,是在与宋军作战时丧生,而杨妙真兄长杨安儿,则死于抗金之役。”
王文统道:“易大侠有所不知,忽必烈此次南征大宋,曾下令征调红袄军参战,李璮却推三阻四,找尽借口,未发一兵一卒。如今李璮派张易前来招纳在下,分明是想在山东打造自己的势力,培植亲信,由此看来,此人早有谋逆之心。”
易逐云微微点头,从怀中取出耶律楚材的书信,递给王文统。
王文统双手接过,展开书信细细读罢,说道:“原来易大侠不仅是耶律相公的乘龙快婿,还是元真教教主!”
易逐云道:“先生见笑了。岳父大人曾对我说,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就如卧龙岗上的诸葛武侯,若得先生相助,平定河北指日可待。”
王文统拱手道:“耶律相公实在是过誉了,在下不过一介寒儒,何德何能,敢当如此赞誉。”
易逐云道:“先生不必过谦。我此番前来中都,意在拿下这座重镇,还望先生助我一臂之力。”
王文统闻言,心头一颤,面上却强自镇定,问道:“易大侠打算如何夺取中都?”
易逐云道:“襄樊一役,兀良合台被斩,史天泽全军覆没。如今忽必烈十多万大军被困鄂州,进不得、退不能。郭大侠率襄樊大军在河南攻城略地,耶律齐统领一万二千汉兵进军汉中,与余玠将军的川军会合,正全力歼灭汉中蒙军。吕文德率两淮兵马北上,直逼汴梁。眼下中都兵力空虚,我打算策反史家,收编汉军,掌控中都。届时,还请先生辅佐公主坐镇中都,稳定局势,我则提兵扫清周边。而后挥师南下,趁忽必烈大军尚未渡过黄河,与各路大军会师,将其主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南!”
王文统越听越惊,摇头叹道:“易大侠,此事恐怕过于理想化了。”
易逐云微笑道:“先生何出此言?”
王文统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其一,中都如今防卫森严,绝非兵力空虚。单是王城内,便屯驻着数千精锐,这些精兵强将,足可抵得上数万大军。其二,史家投效蒙古已三十余年,与忽必烈家族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史天泽向来忠义,既已认蒙古为主,岂会轻易背叛?其他汉将,情况与史家类似,各方相互牵制,难以动摇。其三,宋廷软弱无能,宋主胸无大志,只图偏安江南。即便襄樊取得大捷,宋廷也未必会出兵北伐。”
易逐云眉头一皱,心想:“此人眼光独到,所言极是。”
王文统继续说道:“其四,南宋士大夫与百姓,向来轻视北方汉人,即便北方汉人南投,也不过被视作‘归正民’,低人一等。就连辛稼轩这等文武双全之士,在宋也遭人轻视,更何况普通百姓?当年岳武穆北伐,北方汉人百姓毁家纾难,全力支持,可岳武穆愚忠宋主,不顾百姓死活,贸然撤军,致使北方百姓惨遭屠戮。自那以后,北方汉人对宋廷已彻底失望,不再视其为正统。易大侠不妨想想,若真有汉人政权能崛起,我等读书人和百姓,又怎会甘愿依附外族政权苟活?”
言罢,神色悲戚,无奈叹息。
易逐云亦觉王文统所言有理,心下想道:“百姓只为求活,无可厚非。士人们则深受忠君思想束缚,尚未形成民族认同,这倒是个棘手难题。”
当下说道:“先生不必忧虑。我元真教以驱逐蒙古、推翻宋廷,用武力建立新政权为宗旨,这新政权属于元真教与天下百姓。如今蒙古统治尚未稳固,正是元真教发展的大好时机,若等其根基稳固,再想将其逐出中原,只怕难上加难。”
王文统拱手道:“易大侠志向高远,在下钦佩不已!”
易逐云瞧出他对此并无兴致,寻思道:“看来我这番宏图愿景,只能说与那些热血未脱的少年听,像这等老谋深算之人,根本不为所动。”
话锋一转,问道:“崇文观的高先生被蒙古人与番僧掳去,不知先生可晓得他们将人囚禁于何处?”
王文统答道:“据在下所知,高先生等人应是被关押在万安寺。只是万安寺防守严密,易大侠前去务必多加小心,切不可贸然行事。”
“多谢!”
易逐云起身,抱拳称谢。
王文统见他欲告辞离去,忙起身作揖道:“易大侠,在下能否拜见公主一面?”
话一出口,抬眼迎上易逐云目光。
昏黄灯光之下,只见易逐云眼神中隐隐透着凛冽杀气,王文统不禁心头一颤,忙不迭作揖解释:“易大侠千万莫要误会,在下的功名乃是先帝所赐予……在下纵使万死,也绝不敢背叛公主。”
易逐云神色稍缓,温言说道:“待我拿下中都,先生再来相见不迟。对了,我听闻红袄军军纪松弛,时有屠戮百姓之举。先生若去了,还望多加约束,否则日后惹祸上身,勿谓言之不预也。”
,!
不再停留,出得地下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