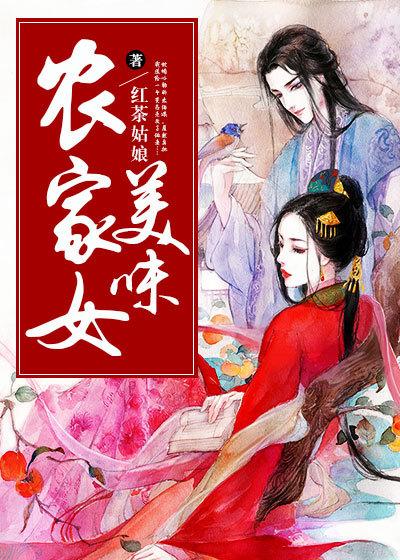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我靠系统称霸后宫 > 第一百八十八章 惊险(第2页)
第一百八十八章 惊险(第2页)
祁元动作迅速,三两下将张铁驴也弄上了驴车。
“你,你怎么把他也弄上来了?他也有十三四岁了,若传出去娘娘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多粟惊呼,她虽也担心这人,却更担忧时虞。
阶级观念根深蒂固,一个小孩终究是比不上皇后娘娘的名声的。
“顾不得了,他若是不跟着娘娘,必死无疑!就凭张家,哪里请的起好郎中?不如直接带回去让御医给看,说不定还能跟着好好养呢,起码也是救驾有功之人。”祁元招呼暗卫一声,“快走!”
张铁驴的父母亲人在驴车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哭,跑的鞋都要掉了。
祁元掀开帘子看了张家几人,扬声招呼着他们:“张伯,张婶子,俺们带铁驴去看御医,一定把他救回来!”
张家诸人还是哭,还是追,追着哭着,张母直接哭晕在地,张铁驴的兄姊们护着张母,张父却还在哭。
多粟看看祁元,再看看外面的张父,只一眼,祁元便知她是什么意思,连忙开口:“不可!多粟,我不能去!”
“铁驴毕竟是为了保护娘娘,你不用带他们入宫,就去安抚安抚他们的心。”
“那也不行!”祁元言辞郑重,“娘娘遇刺之事事关重大,宫中本就布满了眼线,娘娘身边若没人跟着帮衬,被有心之人趁机钻了空子就麻烦了。”
祁元神情中满是担忧,看着平躺着的张铁驴,他的肤色和嘴唇皆呈黑紫色,显然是中毒之态:“而且,我也不知他若是……该怎么跟张家人说。”
一句话,令驴车中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了车轱辘压在地上的滚动声,让人心焦又不安。
很快,几人就看不见张父的身影了,又很快,方才散开的暗卫涌过来几人,皆守在驴车外面还有一人便守在了车帘门边。
他泛着冷意的眸子瞥了眼车板上的张铁驴,伸手探了探鼻息,又在勃颈处停顿片刻,再瞧瞧舌苔和眼底,便神色如常的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了一粒药,掐着张铁驴的下颚将药塞进去。
全程多粟和祁元也没敢说话,那暗卫也不说话,车厢中静的厉害。
多粟急的浑身冒冷汗,将时虞牢牢抱在自己怀中,感受着她冰凉的手指紧握自己的手,掐的手指尖都泛白了,心中的慌乱感更深。
驴车急急忙忙的往皇宫奔去,他们行的着急,压根顾不得疏散群众也顾不得掩藏身形,不少人都看在眼中,纷纷议论这是怎么了?
有眼尖的看到这驴车往皇宫去了,偷偷瞧着竟见这驴车连停都没停,直接驾着驴车就进了门,这得是多急的事情,才能直接驾着车进门?
有人将这疑虑说开了,顿时就有人道:“看着像是送人进去,急的很了,我方才见御药局的几位御医也陆续进宫了。”
“什么?宫中不是有御医吗?怎么又召御医进宫?”
“我看是出事了,但什么人能惊动这么多御医?难不成……”
“瞎想什么,那位就是有事情,也不至于是从宫外送进去,方才那驴车明显就是从宫外送进去的,瞧骑得多急?”
“宫外的……莫不是皇后殿下?!”
“嘶——有可能!我今儿还见草堂书院的学子一起出了城,这么一想起来,那辆驴车怎么那么像我家对门那家学子的驴车呢?连车帘都一样,难不成是草堂书院……”
后面的话没人说,却人人心中都有了决断,一时之间,草堂书院成为众矢之的。
从一开始暗地里议论,到皇帝命人封了草堂书院,将一众学子皆关了起来,草堂书院彻底被搬到了台面上。
连带着被搬上来的,还有前户部大司农杨先!
宫外的杂乱压根影响不到宫内的秩序,在时虞出事,立马就有暗卫率先奔回来告知了颜宁知所有事,颜宁知也不敢耽搁,在时虞还未进宫之前,宫中便都已准备妥当。
驴车刚停在御风阁门口,颜宁知便动作迅速的冲上来,掀帘抱人一气呵成。
御医们迅速跟上,御风阁虽乱却有序。
多粟和祁元也终于能腾出空来,两人将张铁驴抱去了御风阁侧殿,这里早有御医候着为张铁驴治病。
只是,御风阁上空的氛围却不好,似是浓罩了一股死气。
颜宁知冷脸站在屋中一角,将空间腾出来给御医们瞧病,结果瞧完一个便跪一个。
淅淅沥沥的跪了满屋。
颜宁知眸中冷气森然,目光如刀般扫视一地的人:“你们不去给皇后看病,这是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