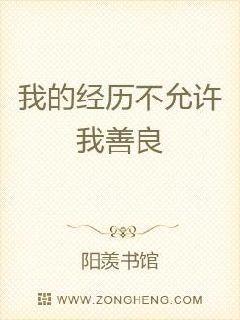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雪下轻卿[先婚后爱] > 7 12日的更新(第2页)
7 12日的更新(第2页)
“你打电话的声音那么大,总不能怪别人听到。”
沈卿轻扬了下眉尾,想起来十几秒前自己确实在和尚灵通电话,控诉她放自己鸽子。
评弹是老调,现在看这些的人并不多,观众席上有一大半的位子都空着。
沈卿觉得季言礼貌似心情不错,不然也不会听曲的途中就评弹和昆曲的调子跟她聊了几句。
“那天回去,你哥怎么说?”季言礼把杯子放下,突然问起几天前的事。
沈卿手在膝盖上敲了敲,想了下回:“我哥让我别在外面乱亲野男人。”
话音落,换来季言礼两声低笑。
他左手手腕扣了块表,黑色的皮带,表盘有一圈很低调的碎钻。
沈卿觉得眼熟,几秒后想起来年初在一个秀场见过。
季家家业大,人丁却很单薄,到季言礼这一代,嫡系这脉就只有他一个人。
甚至于父母早逝,往上再数一辈,只有一个爷爷还在。
唯一剩下的老人常年住在淮洲近郊的某处宅屋,不大爱出门。
所以严格来讲,除了季家那颇多的旁支外,季言礼很多时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人。
“是骂你了,还是骂我了?”季言礼问。
沈卿口气无奈:“都骂了。”
戏院露天,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有戏班子的人送来了几盏秉烛灯。
沈卿把灯接过来时,听到身后的人说了句:“那我有点亏。”
“事没做,却背了骂名。”季言礼低头喝茶。
“也不算吧,”沈卿坐回位置上,低头划了火柴去点灯,“毕竟是我先说我想的。”
沈卿偏头,被烛火染得发亮的双眸定定地看了季言礼两秒,弯着眼睛这么说。
“想什么?”季言礼笑意很淡,视线不偏不倚地落在远处的戏台上,回了这么一句。
沈卿避开这话题不答,几秒后突然俏皮地来了句:“想,怎么让你也喜欢我。”
她话说得实在太直白,让季言礼不得不收了落在戏台上的目光,看过来。
沈卿顶着他的眼神垂头,继续点下一盏灯,嘴里念叨:“这么惊讶干什么,我喜欢的很不明显?”
沈卿说这话时眼睛里的揶揄很重,让人一时有些分不清,她这话里的真意到底有几分。
一曲结束,散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季言礼在旁边小院有个饭局,两人间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道别就已经分道扬镳。
等季言礼吃过饭,和友人道了别,再从隔壁小院出来时,不期然的,再次遇到沈卿。
彼时季言礼坐着的车才刚开出去几米,一声短促而紧急的刹车声,季言礼的身形跟着往前倾了半分,紧接着是前座副驾驶上林行舟的声音。
“好像是沈卿。”他指的是引发这场事故的人。
季言礼放下手里的东西:“撞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