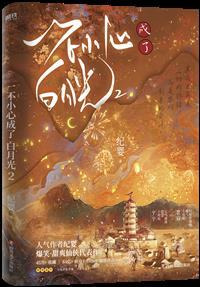墨澜小说>与君同 > 第354章(第1页)
第354章(第1页)
“一切安排妥当。”这一月的风霜雪雨,让傅青眉宇间的少年气褪去了不少,“他们都已经换上了北境的衣装,跟着那些逃兵离开了。”
“好,尽快把船修好,再去搜些羊皮筏子,若是明日午时船还是动不了,我们就乘筏强渡。”
今夜强渡也并非不可,只是没有大船他们就只能用筏子飘过去,他们倒是过去了,那些战马和重甲却必然得翻在河里。要是布衣过河,到了那头还得再去强抢,实在是太过麻烦。
况且暂时被堵在这也好,他们人困马疲,需要好好休息一会儿养精蓄锐了。
“奔袭一月,这两日就好好休息吧。”谢樽转头看向三三两两靠在火边煮饼的士兵交代道,“这边物产丰饶,你带人去他们粮仓搜刮一番,好好吃上一顿。”
渡口灯火三三两两亮起,将寒气隔绝在外,餐风饮露许久的众人终于得以休憩一番。寂静无声的风雪中,谢樽独自站在码头,透过风雪看着隔岸模糊不清的火光,
五百里外,朔方郡一片背风的山坡下,灰白的军帐被烈风吹得摇摇欲坠,完颜昼一边咬着肉干,一边看着那空白良多的简略地图皱眉。
“七座高地关堡勾连支援?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能修出那么多?”
“回王上,我们的人都打听过了,据说这些堡垒自那个陆景渊当上太子的时候就一直修着了,只是这一个多月才在附近低地上挖了拦马壕沟,那些壕沟破破烂烂,起不了太大作用。”
“哼。”完颜昼冷笑一声,“他动作倒还挺快……罢了,那些什么堡垒战线是乌兰图雅的事,不用管,本王只要想办法把陆景渊给宰了就行了。”
“都半天了,出去的斥候回来了没?”
“没有。”那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说道,“一个都没回来。”
“要么丢了,要么死了。”风雪天里这种事太过平常,完颜昼神情淡淡,将羊皮地图收了起来,“不必再等,再过一个时辰就拔营出发。”
趁着这两日风雪不停,他们要顺着无定河南下绕到虞朝后方见机行事,至于陆景渊究竟躲在了在什么地方,进去了往高处走,自然能够找到。
他必然会像乌兰图雅一样在最高处统御全军,挥舞着风雪中最艳丽的大旗。都是活靶子罢了,就看他和谢樽谁有本事先声夺人了。
又是一日过去,天边翻起灰白时,陆景渊坐在某座平平无奇的石堡中,瞥了一眼地上结了一层霜白的头颅,将手中的战报扔在火盆中烧尽。
“当做不知道,放他进来。”陆景渊摸着一旁奉君毛茸茸的脑袋说道,“一万……即刻告诉陆印,让他埋伏到红柳河谷,待完颜昼沿河入境,杀。”
“是!”身着螺纹白衣的青年领命,拎着那颗脑袋就转身离开了。
众人离开后屋中很快恢复沉寂,连风声都几不可闻,在寒冷的石堡中火盆也带不来太多暖意,陆景渊把双手都塞在了奉君脖子底下取暖,随后不出意料地收到了几个大大的白眼。
奉君低声呜咽了一声,把脑袋换了个方向摆放,坚决不让陆景渊蹭到他柔软温暖的脖颈。
“你说他把你送过来做什么?”陆景渊对奉君冷淡嫌弃的态度毫不在意,捏着它软弹的耳朵说道,“不就是来给我取暖的吗?”
一月前谢樽离开武威前差人把奉君给送了过来,明面上说是帮他看家护院,顺便暖暖手。实际上却是让他看好奉君,别让它四处乱跑。若是它留在武威,必然又要闲不住跟着谢星辰四处征战。
原本陆景渊是将它留在了长安的,但没被笼子关着的奉君显然阳奉阴违地跟了过来。谢樽离这里太远它实在找不到踪迹,便只能捏着鼻子跟上陆景渊这半个熟人了。
“不然你还能如何?上阵杀敌?”陆景渊看着它耷拉着的脑袋好笑道。
奉君似乎听懂了他说什么,瞬间瞪大了眼睛,龇着牙就站了起来发出呜呜的警告声,伸出的利爪也在石板上划出了数道深痕。
陆景渊对它的威胁熟视无睹,忙里偷闲地耐心解释道:“战阵中穿梭与平日不同,没有开阔的土地和隐蔽的山林,即使你能屠杀乾部的影卫,战场上也定会被乱刀砍死……别再惹他担忧。”
昏暗的烛光下,奉君那棕灰色的狼眼中闪着点点微光,它端详了陆景渊片刻,最后喷了一下鼻子,扭头顶开未关严的门跑了出去,消失在了漆黑的廊道上。
奉君不喜拘在一处,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也是常事,此番赌气离开陆景渊也没太放在心上。长夜渐深,他轻轻起身合上木门,躺上床榻熄了烛火,用力握住了胸口早已温热的玉璜。
陆景渊目光虚无,轻飘飘地落在远处的黑暗之中,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几乎要跃出胸膛。
即使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他也依然在害怕,怕死,也怕用尽全力也依然黄粱一梦,大梦成空。
如果输了……不,他们绝不会输。
建宁十一月三十,持续了四五日的风雪终于渐渐止歇,而后柳絮似的的细雪纷纷扬扬又下了一两日,待到十二月初方才结束,当阴沉了数日的天空终于雪霁云开,乌兰图雅的大军也已然近在眼前。
数日的风雪让高天澄澈如洗,广阔天地一览无余,站在关堡的烽火瞭望塔上,陆景渊已经可以看见远处的大地边缘筑起了座座营地,虞朝的风雪太小,远远不似阿勒泰那般遮天蔽日,更无法阻挡北境的脚步。
而垂眸望去,脚下的大片平整的土地上,一面面上书朱红虞字的玄色大旗在风中振动,虞朝的将士有六万之众分驻于各个关堡之前,视死如归地看向前方,等待着以攻为守,歼灭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