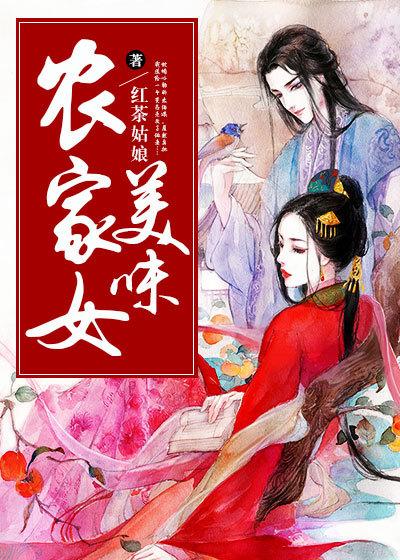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HP同人)红娘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噢。」harry臉紅了,手指勾著自己的杯子。「這也是我喜歡的泡法。我不是──只是習慣,僅此而已。」一陣尷尬的停頓,harry靠在櫃檯上,目光低垂。to瘋狂地想伸手抬起harry的下巴,然後大聲尖叫:「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夜,你甚至不敢直視我?」。to討厭自己居然會這麼想,特別是在他知道harry是什麼的情況下。harry是紅娘的另一半。事後回首,一切都如此清晰。他之所以會知道,一部份是由於慢慢回憶起hestiajones的報告。harry看上去很單純、深櫃、養了一條狗,具有化學背景──棺材中也缺少錄音設備,而紅娘需要讓自己涉足犯罪現場。每塊拼圖似乎都接上了。看到harry的櫥櫃裡的氯仿更是讓一切板上釘釘。起初他不想相信,但to──在所有事情之上──是個警探。他演繹跡象,他再也不能忽略它們了。to發現自己鄙視起自己曾宣誓過的誓詞,發誓尋求真理和正義。他不想考慮在這間房子外面發生了什麼,無論是把harry瘦弱的手腕銬上手銬,帶去法院,還是看到他在精神病院裡凋零。to唯一的可取之處是知道harry很明顯不是獨自犯案。to對自己和眼下狀況感到沮喪,讓自己的眼神遊蕩。他偷來的小蒼蘭裝在花瓶裡,花瓣皺了,經過一夜枯萎,顏色幾乎是灰的,但是harry看著它們的樣子──眼神柔和,粉紅色的嘴唇掛上微笑──讓to以新嶄新的角度看待。「早上了。」harry回頭窺向to。「你不是應該??應該去找gny嗎?在火車站?」「我的人可以應付她。我在昨晚來之前向kgsley通報了她的下落,他很高興能結束這場狗屎演出。」harry對髒話眨了眨眼。「他的原句呈現,不是我講的。」harry的舌頭飛快地舔濕他的下唇。他張開嘴,好似要問問題,烤箱卻在這時熄火。「司康好了。」他的聲音高揚。他放下杯子,忙著趕去。帶上烤箱手套,他取出一盤新鮮出爐的司康,房裡滿盈著藍莓和夏威夷果融化的味道。「哇哦。」to非常驚訝地說著。他最後一次吃家常早餐是??老實講,久到數不清了。「你不必這麼做。」「你是我的客人,好嗎?」harry把糕點刮到盤子上,笑著說:「至少我能餵飽你。我本來要做香腸,但padfoot太嗨了,會從你的盤子裡搶走食物。」他在to面前放了一個司康。他喃喃道:「如果這是我的最後一餐,至少這份陪伴值回票價。」to狡猾地無視了那句話,吹去熱氣。他咬了一口,在高溫中品嚐,藍莓在他的舌頭上爆裂。「很好吃,真的很好吃。」harry懊喪地聳肩。「從我還看不懂字母時,我就一直在做早餐了。我的阿姨和叔叔──嗯,你知道的。」to若有所思地咀嚼,做了一個決定。「我好幾年沒吃自製早餐了。」他輕聲傾訴。「我早上沒有時間,即使我有時間,也不會這麼好吃。和我的母親相比,我是一個糟糕的廚師。如今,她能做得不多,可以乖乖吃藥就謝天謝地了。」harry瞪大眼睛,似乎明白聽到to軼事的意義。即使這就像他早晨的例行公事一樣簡單,他正在敞開心房。緩緩地,harry坐到他身邊,雙手托著茶杯。他耐心地等待著to完成他咬著的一口,小心翼翼地選擇用詞,喉嚨震動。他的語氣相當自控、平靜、沒有情感──即使他的睫毛因疼痛而顫抖。「我二十一歲的時候。」他說道,停了下來。他以前從未將這些說出口。「她被診斷出患有白血病,剛開始時症狀很小,只有一些奇怪的紫紅色疹子。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是因為她的血管破裂了。她是那麼容易就瘀傷,晚上會流鼻血,而且體重該死地直落。」一旦他開始了,to意識到自己無法停下來。他抬起一隻穩定的手放在心口上。「最初的幾個月,我嘗試自己照顧她。但是我的生活方式、不規律的上班時間和壓力,這根本行不通。醫生推薦了我母親的護士pofrey夫人──一直以來,她拯救了我們的生活。她確保我每天早上都吃點東西,即便不是新鮮出爐的司康。」to笑了起來,舉起他手裡有點忘記的糕點,果斷地咬了一口,機械性地咀嚼。「她鼓勵我與同事共度時光,試圖幫助我找到工作和母親以外的生活,可是沒什麼用,但是──沒有她,我早就放棄了。醫院的賬單、藥物、治療、poppy的薪水,我不得不加班。當時我的老闆scriour把我突如其來的熱情視為想要升職的意思,退休後,他推薦我接下他的職位,我從來沒有這麼感激過。」to在凳子上移動了一下,低頭凝視著他那半空的茶杯。儘管茶要冷掉了,他還是細細地嚐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