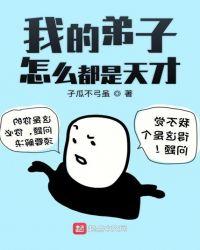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妖怪夫妇探案日常 > 第158章(第1页)
第158章(第1页)
远处传来一声呼唤,“小姐。”那个叫阿初的侍女穿过花海,快步朝这里走来,顿足在尹神曲身边,她微微垂首道:“小姐,老爷让我过来找你,他有事情要对你说。”尹神曲执拗道:“不去不去。”身姿娇小的侍女不卑不亢,又字字清晰地重复一遍,“小姐,别耍小脾气,老爷真的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尹神曲仍不肯动身。花影缤纷,尹晟也从树后迈步而出,他径直走到花涴身边,眼眸中只盛放她一人,“你好,”他紧紧盯着花涴,眼睛眨也不眨,“我叫尹晟,是振武将军的儿子,请问姑娘芳名?”花涴看不惯他的眼神,她往后退一步,磕巴道:“花、花涴。”尹晟顿了顿,“你姓花?”不知想到了什么。继而,又拿故作深情的眼神看花涴,“姑娘可有空,在下想请你喝杯茶。花茶、红茶、绿茶,随姑娘挑,我府上都有。”花涴被他的眼神和热情吓到了,手按在鞭子上,她慌张无措地看向越千城,想向他寻求帮助。越千城快速接收到花涴传达的求救信号。干脆不再试图挣脱尹神曲的爪子,越千城用力扯断衣袖,把整个袖子都送给她。抓起花涴的手,越千城代她向尹晟回话,“没空,你们家的茶不喝也罢。”说完,趁尹神曲还没扑上来,他牵着花涴的手离开此处。日光悠悠照天地,望着花涴和越千城携手离去的身影,尹晟顿觉失魂落魄。良久,他捏紧拳头,重重捶向一侧的柱子,咬牙切齿道:“那!个!男!人!是!谁!”名叫阿初的侍女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翻了个白眼——这家俩兄妹真的不是双胞胎吗?逃离尹神曲和尹晟的“魔掌”,花涴和越千城往落脚的厢房走。刚到厢房门口,他们凑巧碰到问话回来的霍嘉和顾一念。霍嘉的头发一如既往的乱,说是鸡窝都对不起鸡窝,与他相比,顾一念简直干净得如高山上的雪莲花,纤尘不染。停步在门口,越千城问他们,“怎么样?”霍嘉做了个谨慎的手势,示意进房间再说。把房门掩上,他才道:“问出来一些事情。”倒杯温水喝,他接着道:“将军府规矩严,下人们只知道府上丢了东西,却不晓得丢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怕透露马甲胄丢失的消息,只问府中近来有谁表现奇怪。问的人都说,负责厨房采购的房叔近来很奇怪,花钱突然大手大脚的,行事也畏畏缩缩,不如之前坦荡。”拉开屏风,越千城从行囊里取出一件新外袍,在屏风的遮挡下,把身上这件缺了只袖子的外袍换下来,“马甲胄不是小物件,抱在怀里运送出去太显眼了。”系上外袍的带子,他从屏风后走出,“既是府中采买物资的人,出门肯定要带筐具,他可以把马甲胄装在筐子运走。”这是难得的线索,不能轻易放过,越千城思忖稍许,谨慎道:“先别惊动那个房叔,咱们去会会他,看能否查出什么。”少年一举一动都透着洒拓风姿,他身上已看不出任何昔年的痕迹,恍然若重生一场,曾经的懦弱尽数被烈火焚没,只剩下果敢。花涴静静看着越千城的眉眼,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说做就做,没有再耽搁时间,他们即刻去厨房找负责采买物资的房叔。恐去的人太多会引起慌乱,越千城让霍嘉和顾一念在房间休息,他与花涴去厨房找房叔。房叔的年纪约摸四十开外,许是常年在灶房工作的原因,吃东西方便,他养了一身肥膘肉,走动时浑身都晃悠。没给房叔反应的机会,见到他之后,越千城故意板着脸,语气模糊道:“我们都知道了。”房叔有一瞬间心虚,不过很快恢复如常,“什么?”越千城没有漏看他一闪而过的心虚,眸光锐利,他继续逼问他,“老实交代,谁指使你这样做的?”房叔的眼神开始闪躲,“你、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挑起一侧唇角,越千城朝他冷笑,“敢在将军府偷东西,你的胆子不小啊,尹将军纵横沙场多年,最厌恶品行不端正的人,你说,他若是知道你做的事情,会如何处置你?”房叔也是个外强中干的主儿,一身肥膘肉全长外头了,胆子只有手指甲那么大。被越千城这样连吓带忽悠,房叔的心理防线顿时崩溃,“我错了!我错了!”他跪地痛哭,“我不该偷府里的东西卖钱,可……可我欠了太多赌债,靠每月的工钱根本还不上,赌场的人说再不还钱,就要来砍我的手指头,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只能偷府里的东西卖钱还赌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