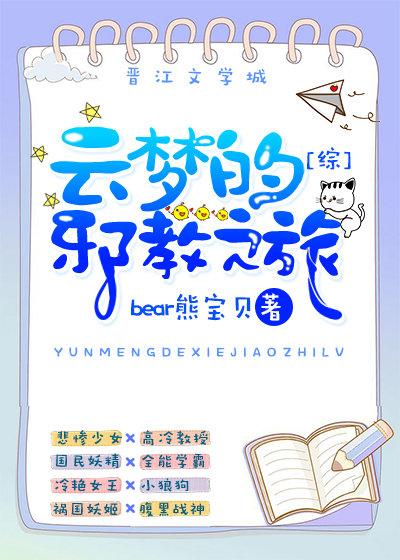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致我那菜市场的白月光 > 第27章(第2页)
第27章(第2页)
这里一不保暖,二不防盗,除了有两块板子挡风,跟躺在野地里睡觉没什么两样。
程厦也特别争气的立刻发烧了。
我铺了四层的被子,还塞了热水袋,借了三个小太阳对着他烤。
他脸通红,只探出一个头来,像只傻乎乎的鹅。
“我好没用啊!”他发出鹅叫。
我安慰他:“没事,我跟他们说你是南方人,没给咱东北丢人。”
“太好了。”他烧傻了,还挺高兴。
我笑得不行,问他:“还要死要活的跟我待在一起吗?”
他很腼腆的笑了一下,用力点点头。
“行了,明天我们就去县里的宾馆了。”我给他掖掖被子,安慰道。
程厦又问:“你在非洲一直住这种房子吗?”
“我们那是长期项目,墙会厚很多。”我道:“不过工地么,环境都好不到哪去。”
但我其实觉得还好。
我长大的那个房子,其实也不过三十几平,还塞满了奶奶捡来的破烂,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又太冷,写作业的时候如果不握着暖水袋,手都是僵的。
所以长大之后,即使再艰苦的环境,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适应。
真正让我不适应的,反而是去那些高端的酒店、觥筹交错的晚宴、包括程厦家。
这都让我手足无措。
就像程厦不适应工地的板房一样。
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无论是我攀上云端,还是他走入泥淖,去对方的世界,都会很难受。
我叹了口气,然后坐到桌前,开始整理今天的资料。
程厦道:“你……睡一会再做吧,如果精神不好,工作效率也会不高的。”
我说:“还有三天就要跟县领导开会了,这些东西必须得弄好,你先睡吧。”
程厦还要再劝,可是感冒药和小太阳的双重功效下,他慢慢地睡着了。
我反复的看图纸,算预算,可是头痛欲裂,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
只能出去用冷水洗了把脸清醒一下。
窗外,是浩瀚到有点可怕的星河,漫天的繁星明亮得像个童话,而不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和烧羊粪缕缕上升的烟气,又时刻提醒我,这是在人间。
我想起我很小的时候,跟着奶奶住过一段时间平房,那是个自行车棚附带的小房间,得烧煤饼取暖,但很暖和,我的小脸总是被烘得红扑扑的。
那里为什么会暖和呢?就因为地方小吗?我想着想着,眼前的星空变成了那一排一排自行车,把手银亮,车铃清脆,飞快地朝我驶过来,
我下意识的用手去挡,可是挡不住,那些星星变作的自行车带着一连串欢声笑语,从我身边嗖嗖的穿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阳光强烈得我睁不开眼睛。
而我正在程厦背上,他正艰难的背着我下楼。
我想问,可是嗓子干哑,根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别怕,我们马上到医院。”程厦把我扶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