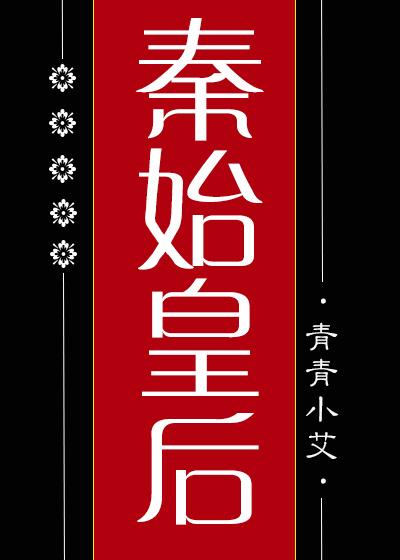墨澜小说>等雪停 > 第17章(第2页)
第17章(第2页)
蒋勋铁骨铮铮,右脚不断蹬打床榻,嘶吼挣扎。
傅云娇拼命按压,身上汗湿了一层又一层。
幸好蒋勋身高足够,傅云娇能用上老办法,她把他的脚腕捆上床沿一角,整个人拉成大字。
反正蒋勋心里早就恨死她了,恨一次和很两次的区别也不大。
傅云娇这么想着,把绒被蒙上蒋勋的眼,说,“蒋先生,对不住了。”
蒋勋的裤脚,一直提到膝上,傅云娇才见到那块模糊的类似圆柱的肉块。
不同于他的断掌,蒋勋的大腿仍然存在,强壮的,与常人无异,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
然而在大腿末端,那一条条伤口像是强行将他的生命力砍去了半截,歪歪横横的,如蠕虫一样,匍在他的断肢表面。
看到这样的伤痕,傅云娇很难不去联想伤痕的主人经历的是什么样的锥心之痛。
她不忍心看下去,取出药瓶,照着赵医生的方法,替蒋勋上药包扎。
蒋勋蒙在绒被中,筋疲力尽,已经再发不出一丝声音。
他的怒火像燃尽的爆竹,炸得声势浩大,可伤不了傅云娇分毫。
蒋勋躺在黑暗里,黑暗放大了他所有感官知觉,放大了碘酒涂在伤口的辛辣,同时也放大傅云娇用手掌一点点包裹他的残肢的温暖。
蒋勋能感觉到,她的手似乎很软,很小,要两只掌叠在一起,才能包裹住他。
她的动作无疑是生疏的,但又有自己的节奏。
仿佛把那截残肢当做生命,用双手与他对话,给予他安抚。
这感觉令蒋勋陌生,又快要令他颤抖。
他情愿对傅云娇是气是厌,也不愿意自己对她带来的温暖产生迷恋。
当傅云娇的手不知不觉来到了蒋勋的大腿骨附近,他的双臀一下绷劲得比石块还硬。
黑暗中,有种莫名的,令他惶恐的躁动愈演愈烈。
像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像天干物燥的火烛。
她搓揉的力道,一下下都极其认真。
一下一下,手掌撩动他的神经,似羽毛,似落叶。
从未有一个异性的双手,离蒋勋的丛林如此接近。
蒋勋颅内闪过一道雪白的弧光。。。
他不是傻子,他清楚地察觉到了自己身体某种东西正在苏醒,某种他本以为不可能会再有的欲念,像沉睡于冰山下的海怪,从他的躯壳里醒来,张牙舞爪。
三年了,纯粹的贪恋,纯粹的本能,无法自欺欺人的欲望。
这样的场景,面对这样的人,它居然苏醒了过来。
蒋勋羞耻难耐。
他羞耻的不是欲望本身,而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欲望源头来自于她。
这羞耻甚至已经盖过他的残缺被她直视的羞耻。
一个人怎么能对自己讨厌的人产生…欲望?
他这样和动物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