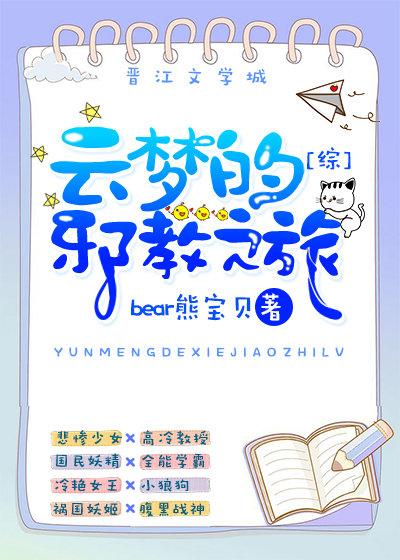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殿下好风流! > 第87章(第2页)
第87章(第2页)
“是啊,这不就是一本白纸么?”有人小声嘀咕。
恭王年纪虽轻,行事却老辣——命徐长青带来这本账簿,令他看得心惊肉跳,看完却是一本白页,他对着一大家子人连个证物也拿不出来。
戴宏达只好生硬冷笑:“这么说是我拿恭王做筏子,用来吓唬大家,让各房出钱?”
那年轻人再狂妄也不敢接这话,另有旁人陪笑劝和,却也有人咕哝:“虽都是姓戴的嫡系房头,可那些产业每年的明细也从没让我们看过。”
“家里姑奶奶当了贵妃、生了皇子,可到现在只有二叔一房人去了首阳,剩下咱们在南边厮混,连圣上都没见过。”
“是啊,我家那小子成日听差遣东跑西颠,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年底分红便是那么一点罢了——外头都说咱们戴氏富甲一方,自家人却没沾上什么好处。”
开始是小声议论,渐渐变成七嘴八舌。
戴宏达听得清楚,并不辩解——也没法辩解,看着乌泱泱一堂的人。
个个算得精明,全只惦记落进自己口袋里的利益,没一个愿意与他分担——也对,戴氏自迁出首阳,在忙于插手盐铁、搜罗私产的漫长岁月里,早丢下原先的世家风范传承,蜕变成商人。别说年轻一代,就连自己这辈也多是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戴宏达的儿子替他打抱不平,忿忿道:“你们各房头各自分管不同产业,怎么叫没沾上光?平日你们没少贪公中的钱,倒是一声不吭;这会不过叫你们一起拿点出来,大家共渡难关,就这么多抱怨?!”
众人一听这话炸了锅:“谁贪过公中的钱?!你倒说说清楚!”
“伯父没少把公中的钱送与外人,打点官场便罢了,还借给谢家——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从来不对付——这岂不是长他人势力打水漂?”
戴宏达身心俱疲。
祖坟冒烟,这一辈里二弟戴宏远考得功名,但首阳城中无人帮衬,世家暗地里觉得戴氏低人一等,全靠家里花钱结识朋友,拉着妹妹裙带,一个辛苦爬到户部尚书的位置、一个成为宫中贵妃,相互支撑——他们倒是想提携自家子侄,可惜戴氏族里再没一个能考上功名的后辈。
一代不如一代。
这话老父在世时常常骂他,戴宏达看着吵闹不休的一屋子人,忽然也很想这么骂一句。
也有略清醒些的,赶上来问:“那贵妃怎么说呢?叫三殿下赶紧御前告状,把这二皇子撤换了!”
戴宏达重重叹气:“昨日收到传信,贵妃最近不知为何事惹圣上厌烦,三殿下倒是没被牵连,可哪能在这当口叫他替母家说话?避嫌还来不及。”
有和戴宏达平辈的,愤然道:“当初为把贵妃捧进宫,海量的银子花出去打点,之后每年也都没少孝敬,如今出点事,就不管咱们了?”
“行了!”戴宏达终于耗尽耐心,一拍几案:“这算个什么事?!不过花两个钱消灾罢了!上次你儿子在酒坊打死了人,上下打点了五六万两,公中不是出了一半?!首阳也不是贵妃一人说了算,别什么事都要贵妃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