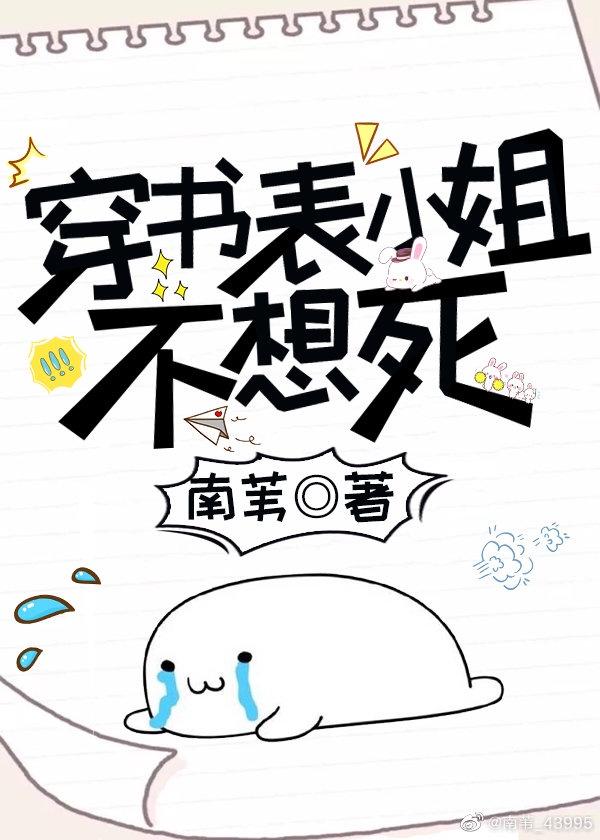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心理大师 > 第33章(第3页)
第33章(第3页)
“可是什么?”我追问道。
霍寡妇抬眼看了我一眼:“可是五军看到我似乎并不高兴,相反,在他第一眼发现是我的时候,脸上的笑都挂不住,好像很失望一般。聊了半小时,他也没说什么话,就瞅着我胳膊上戴着黑袖套,随便问了句是不是又守寡了。我应着,然后我以为他会安慰我几句什么,谁知道他扭过头压根不看我了。”
“他在看到你的时候露出很失望的表情?”我小声复述道,“也就是说你与他本来期待出现的探望者并不是同一个人。”
我扭头望向了邵波,邵波也紧皱着眉头对霍寡妇发问道:“你能确定不会有其他人去看他吗?”
霍寡妇摇头:“不可能有的,他无亲无故,甚至连一个能一次性说上超过五句话的人都没有。”说到这她又想了想,似乎在确认这一结果。最后她很肯定地说道:“不可能有的,绝不可能有人会去看他的。”
17
我们和霍寡妇在那小小的包房里聊了有两三个小时,话题始终是围绕着田五军的。渐渐地,一个话不多、孤僻固执、为人处世存在很大问题的光棍汉子在我们脑子里逐步成形。至于寡妇挂在嘴边的算命先生所说到的命理论,在我看来,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面相学说,在中华文化产生之初,便开始酝酿并逐步成形了。根据一个人五官与外表的一些特点,来揣测人的性格。而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也基本注定了这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西方科学与之对应的,便是犯罪心理学萌芽最初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意大利医生龙勃罗梭(cesarelobro,1836—1909)撰写的《犯罪人论》(l’uoodelente,1876),内容很大程度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延伸开来的。他将犯罪人外形上的特点,诠释为遗传缺陷,并认为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东方的心理学家将《犯罪人论》看完后,再对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相学会发现,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基础是人类已经确定的各种论据,后者为天马行空的神来之笔。
于是,前者成了科学。后者沦为封建迷信。
到吃得差不多了,似乎该聊的也聊完了,邵波最先站起来,对着楼下喊话:“老板娘,买单。”
楼下传来那女人的声音:“好嘞,已经算好了,258块。”
这时,霍寡妇却率先走出包房往楼下喊:“老板娘,这顿算我的。”
楼下似乎没听见。
邵波追过去:“嫂子你别闹,怎么可能让你请我们吃饭呢!”
说话间,大家都到了一楼。只见霍寡妇已经抢先到吧台前拿起了账单:“算我的吧,不过我身上钱不够,从我这个月工资里扣。”
“还怎么扣呢?”吧台里的女人阴着脸,“前些天你娃住院,已经支了这个月工资,现在这算啥?算赊账吗?”
邵波三步两步上前,掏出三张一百的递了过去。紧接着又犹豫了一下,多拿出一百来:“这位大姐,不用找了,多的算小费。下午我们想让嫂子领我们去一趟大哥坟上烧炷香,没问题吧?”
吧台里的女人喜笑颜开:“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她说完对着霍寡妇嘀咕了一句,“去吧,不算你请假,也不扣你工钱。”
寡妇愣了下,嘴角往上翘了翘,最终硬是没笑出来:“那一会儿我娃娃……”
“你去吧,娃娃放学回来了我让他上楼上,自己做作业。对了,你们村子远,如果晚上你回不来的话,我让你娃跟我娃睡一晚就是了。”老板娘继续说道。
我们走出湘菜王的时候是下午1:11,以前文戈说过,如果一个人无论有意无意看表,看到的都是好几个“1”的话,那就说明他很孤独。
我是不是孤独我无法确定,因为我身边始终有一群要好的朋友。
但……我每次看表时,都能看到很多个“1”。
霍寡妇扬起脸看了看天:“你们是真想去看看我那第一个死鬼男人的坟吗,还是想去看看田五军以前的家?”
“后者。”我很老实地回答道。
“你们一点都不像公安,公安不会对人这么和气。”霍寡妇念叨着。
“我们确实不是公安。”我点头。
“可以给我说说你们的目的吗?算了,我也不想听了……”霍寡妇朝着街道前方看了看,“我们坐那种蹦蹦车过去吧?不贵,到田五军那破房子只要30块钱。”
她说的蹦蹦车,其实就是带斗的三轮摩托。司机见我们是城里人,开口要50,来回100。霍寡妇一顿数落,最后还价到了来回50块。可邵波天性大方,败家是常态,递给了人家100,说不用找了,给开稳当点就行。
寡妇和司机都愣了一下,两人差不多10分钟的拉锯战似乎没啥意义。
蹦蹦车便驶出了虎丘镇,开上了蜿蜒的山路。所幸南方的山都不陡,起伏不是太大。古大力以前应该没坐过这种三轮摩托,看上去比较兴奋,那颗大脑袋东张西望,嘴里不时小声嘀咕着什么。到某个颠簸得厉害之处,他又正好摇头晃脑得太狠,一不小心差点往车斗外面翻下去。多亏邵波反应快,抓住了他的皮带给扯了回来。平衡能力有着严重问题的大脑袋男人满脸苍白,至此没有那么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