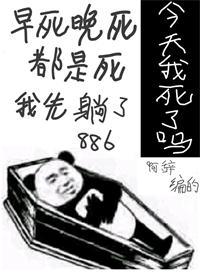墨澜小说>杀了县令我就跑 > 探深浅(第2页)
探深浅(第2页)
但多年行走江湖的直觉,却让秦烟生疑,往往越是滴水不漏,反而深不可测,既然他出身贫农又喜读书,那是何时学武,又是何人教授他?虽然未曾见过他动手,但见他走路脚不染尘,可知他轻功不俗,甚至有刻意隐藏之嫌。
书房中。
秦之行琢磨着秦烟与张鸢的联系,怕她故意隐藏身手,他授意顾一,试她一试,从她的反应来看,确实不会武功,许是他多疑,人有相似也不无可能。
“咚咚咚”敲门声起,秦之行看向门外:“何人?”
秦烟推开门,身子还未进,只露着脑袋在门边:“大人,午时已过,厨房备好饭菜,我来请大人移步膳厅用饭。”
“好,下去吧。”
因他向来不与众人同席用膳,所以书房隔壁专为他设下膳厅,膳厅也放置着香炉和炭火,屋内溢着暖意。
秦烟摆放好碗筷,坐在一旁,眼神瞥向隔壁书房,嘴里嘀咕着准备好的说辞,做好随时被赶出去的准备。
未久,隔壁开门声起,秦之行信步而来,看到坐在桌边的秦烟,没有进屋,私是不快:“你为何在此?”
秦烟讨好似得笑着,起身为他搬开椅子:“我帮忙送饭,看见就一副碗筷,怕大人刚回乡,自己独食未免寂寞,来陪陪您,”见秦之行没有动作,她弱柳扶风地扶着额头,又编出一个理由,“我这前些日子身体不适,大夫说不能受寒,我们那屋太冷了,还是您这暖和,大人您心胸宽广、心怀百姓,该不会介意我在此吧。”
也不经他同意,秦烟又坐回椅子中,巴巴地望着他,心道:这饭她吃定了。
秦之行只觉她聒噪,丢下一句:“食不言寝不语。“随后落座。
秦烟见他甚是谨慎,先拿银针一个个菜试过,其实厨房在送来之前都已经验过毒,几经人手,这其中可操作的环节太多,况且,他面前这个“秦烟”疑点太多。
看着银针都未变色,他才开始动筷。
秦烟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冒然行事,还是先探得虚实,再行动为上策。
李大厨的手艺自是没得说,秦烟吃得认真,又不能说话,只偶尔用余光瞄他一眼,却发现秦之行每下一筷,夹得都是自己刚刚动过的地方,哪怕天家圣人也不至此,她心头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寒意,汗毛也随之轻轻颤栗。
她草草扒了几口饭,此等心细如丝,出手杀他,可真不是件易事。
吃完后,他喊住秦烟:“下午你随我出去一趟。”
秦烟应下,整理好碗筷后,还没休息片刻便出门了。
此行只有他们二人,秦烟坐在马场上,迷糊中她又做到那个梦,梦中人还是重复着一样的话,待她清醒过来,看到秦之行气定神闲地坐在一旁,问道:“又头疼了?”
“小事,昨晚没睡好。”
不久马车停下,秦之行有意让车夫把马车停到远处,秦烟跟着他走向湖边走去,心里却纳闷,如今县衙人手充足,为何他总是喊她随行:“大人,您怎么不带师爷一起?”
秦之行在前方走着:“怎么?你不愿来?”
气候回暖,之前结冰的湖面,已有不少冰块裂开,露出幽墨深邃的湖水。
秦烟四下打量着周围,郊外、无人、河边,远处的车夫已然不见身影,心中盘算:正是动手的绝佳机会,完全没听到秦之行的疑问。
秦之行继续道:“县衙当值虽有时辰,但遇到突发情况务必随叫随到,你既已经答应,自当先明白这些,我对李玉还有其他安排,你可还有疑问?”
秦烟心不在焉地点头,嘴上应和:“没有疑问,”她选定了一处开阔的湖面,周围没有碎冰,“那大人为何来此处,总不能来观景?”
“上任县令正是死于此。”
“溺亡?他杀?”
“仵作验尸结果是溺亡,但他死之前渝州大旱三年,当时的水位定不比现在高。”
秦烟摇了摇头:“这只是你的猜想,没有真凭实据,何况老县令一生勤恳,也从不和人结怨,这湖水深不见底,我们也不知其深浅,”
她边说边故意往那处走,秦之行在他身侧走着,思索着她的话,未注意脚下。
秦烟见他出神,继续给他讲老县令的事,见他走到自己心中的位置,她向他身边悄悄挪近一步:“我倒是有一计,可以探探这深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