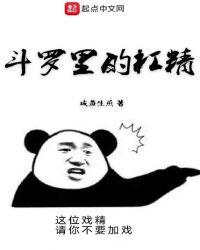墨澜小说>战国:让你弱国苟活你却逆天改命 > 第1158章 鎚杀贵沙(第1页)
第1158章 鎚杀贵沙(第1页)
孟语换上中原裙衩,亲自走上城头,以中原之礼,向着白幕盈盈一拜:“敢问将军高姓大名?归属何部?”白幕一愣,没想到义渠城中居然还有中原女子。但看此女仪容不俗,义渠人对其毕恭毕敬,遂也保持几分礼仪,反口回问道:“芳架为谁?焉何在此?”孟语款款而回:“老妇秦献公之未亡人,公子虔之母。老妇托大,贵国之主,合该称老妇一声舅母。”白幕一惊,端木将军临行前再三叮嘱,让自己寻找、并善待这位孟语夫人,不曾想以这种方式相见。白幕立即毕恭毕敬地向城上施礼:“外臣白幕,参见夫人。我部乃端木将军麾下之朔方军,奉令南下,讨伐义渠,冒犯之处,夫人见谅。”孟语一听是端木伯御率军而来,对自己母子的平安更加放心,但身后满城义渠人,有些事她还是要问上一问:“义渠与汉,素无瓜葛,不知汉王因何兴师,讨伐义渠?”白幕道:“贵沙弑杀君父,人神共愤,如此禽兽之君,人人得而诛之,故汉王命我部,兴师南下,吊民伐罪。”这理由都是现编的!朔方军出兵的时候,端木伯御都没想好讨伐义渠的理由。就是本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念头,现走现说。行至半途,贵沙弑君。好啊!这么现成且高大上的借口,不敢浪费了,必须堂而皇之地用起来啊!孟语冰雪聪明,更知道端木伯御与公子虔交情匪浅。当年孟语住在成都,端木伯御都是以子侄之礼前往拜见的。今天这位白幕将军彬彬有礼,就显示了端木伯御的态度。孟语道:“贵沙王果然战死?”军机大事,白幕不可能向孟语吐露实情,他钢牙一咬:“果然!”“端木伯御将军今何在?”“少则三日,多则五日,大军必将抵达。”“好吧。白将军,老妇有一不情之请。端木将军未来之前,还请贵军不要攻城。”白幕略一思索:“善!不过,义渠人亦不得对我军有丝毫冒犯,否则,大军攻城,鸡犬不留!”就这样,白幕与孟语达成了城下之盟。郁郅城前。端木伯御的拖延战术,成功激起了贵沙王的好胜之心,放着大队人马不用,专心和端木伯御斗将。一个手持大鎚,要将世界砸得粉碎;一个手持九齿钉耙,要将天地撕裂开来。两人恶战三日,端木伯御心念一动,盘算白幕与当奇应该已经得手,当下招式一变,攻势变得异常凌厉与刁钻起来。如果单纯是比拼气力,贵沙王完全可以应付。当伯御的进攻开始多变与幻化,贵沙王明显感到了吃力,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招架,反而打乱了原有的进攻节奏。端木伯御冷哼一声,暗道:贵沙,老子不陪你玩过家家了!两人战罢一个回合,再次拨马相向,打马发起新一个回合的冲锋。贵沙钉耙高高举起,眼中冒着凶光,恨不得一耙将端木伯御给砸成满地碎骨。但这样一个姿势,却中路大开,将胸腹部位敞亮地露了出来。端木伯御将右手鎚使劲抡了几圈,突然脱手,玄铁大鎚好像一颗炮弹一般,以巨大的加速度飞向贵沙大开的中门。贵沙未料到端木伯御居然还有一招“撒手鎚”,在义渠人的心目中,武器几乎是身体的一部分,到手都不能撒手的。“怦!”的一声,玄铁大鎚正中贵沙王的胸口,在巨大的撞击之下,贵沙王一口老血喷射而出,庞大的身躯被撞得飞离马背。贵沙王的马匹继续保持着全力冲刺的速度向前,而贵沙王则保持着抡耙的姿势向后倒飞而去。端木伯御左手鎚交至右手,双腿一夹,大青马心领神会,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加速冲上。贵沙王的自由落体运动还没有结束,端木伯御如同一道闪电般快马赶上,一招海底捞月,抡鎚将贵沙的身体砸向天空。贵沙王亲耳听到了自己骨骼崩裂的声音,整个身体如同皮球一般,冲天而起,手中的九齿钉耙也飞了出去。伯御眼睛死死盯着贵沙王的飞行动作,口中已然高声下令:“全军冲锋!”这些天来,端木伯御打得高兴,朔方军这些纵横惯了的骄兵悍将早就被憋坏了,伯御的“锋”字还没有说完,大队骑兵已经呼啸着从身边冲了过去。贵沙王的身体像个沙包一样落下,端木伯御目不斜视,抡鎚又是一下,将贵沙再次捧上蓝天,如此反复,反复如此!贵沙你看,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飞上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飞吧,一直向前飞,别往两边看……贵沙这张大脸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在义渠王城之下。端木伯御将贵沙的身体砸成大肉饼,但每鎚下去,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他这张脸。刚刚失去了老王,新王又被抛掷式秒杀,就算相信战死吉祥的义渠人,也慌了神。端木伯御率领的朔方军本部,是精锐中的精锐,正好拿这些义渠兵祭了祭马刀。一场混战下来,义渠人战死一半,生俘一半。这还是端木伯御坚持“降者不杀”理念才留下来的,因为广袤的河南地,前套、后套、西套平原,都有大量肥沃的良田,需要人口去开垦。征服即可,多杀无益!和上次白幕拿一颗假人头糊弄不同,这次端木伯御下令将贵沙王的脑袋巡城一周之后,直接扔进了城内,让王城内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就在王城之内一片大乱、人心惶惶之际。倾国阏氏孟语,青衣轺车,孤身出城,愿为阖城居民之安危,与汉军进行谈判。满城义渠人肃然起敬,沿路拜送这位义渠唯一的“主心骨”出城。时值天降细雨,恰逢国将不国,竟添无限悲壮之感:()战国:让你弱国苟活你却逆天改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