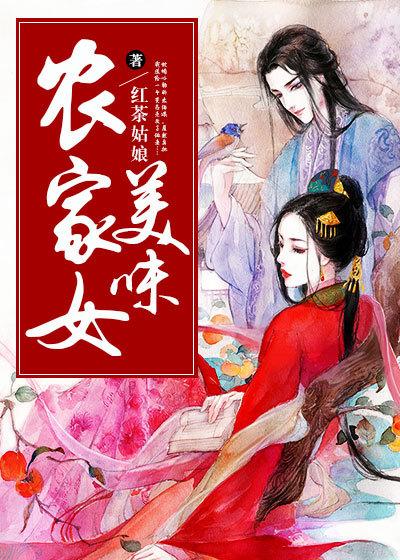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像雏菊一样脆弱的我们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你是不是有病。”
我披着毛毯,在父母的陪伴下走出警察局,看到了她。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却出乎意料地听到了她这么说。
欸?我不解。
她低着头,黑色的长发垂下,背对着夜间的月亮与路灯,看不清表情。她没有看我,自顾自的说着。
“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伟大很善良。你觉得,你代替了我被他们强奸了,我就该感激你么?我就能变的和你一样么?真恶心啊,你。还恬不知耻的说自己性瘾。真的是,你,还有一点起码的羞耻感么?”
她抬起头,微弱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扭曲的模糊不堪。只有脸颊旁边大滴大滴滑落的泪珠,反射着晶莹的光,才那么真实。
“真的是,你真想保护我的话,直接报警就行了啊。我不想我被强奸的事情被其他人知道,可都那样了知道也无所谓了吧。但是你呢,就这么把自己送出去了?什么啊,你想过我没有。我不是你这样的垃圾啊。我也会愧疚的,你让我以后怎么生活啊?到底。”
她走向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肩,捏的我生疼,表情狰狞而扭曲。我想尖叫,但我看着她的泪流满面大脑就一片空白,我也不知所措。
“你真的,好恶心。那晚我都说了过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滚啊,离我远点啊,变态、混蛋,不要再恶心我了啊!!!!”
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就这样一片混乱的跌倒在地,我看见她独自一人消融在夜晚的黑暗里,我记得那条路,回到她那个只有她一个人的家里去。
我的父母走过来,将我扶起来,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瞪大眼睛看着我父母那陌生而又熟悉的脸——正常的夹杂着悲哀与疑惑——但我仿佛不认识他们一样认真地端详着,我说:
“………没事,她只是有点害怕。我们回家吧。”
我也回家了。
我申请了休学一段时间,我的父母对我这一决定颇有微词,但在学校方的坚持下,我成功了,我父母甚至因为这件事和老师多次沟通、甚至与争论。
然而实际上我在家里只呆了大概一周多一点,等我和我的玛格丽特一起到学校时,同学、老师、我的父母都以一种惊诧的眼神看着我。
而只有她站在我身边陪我,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在前几天还能正常的进食,只不过会经常发呆。
而当父母问我准备多久回到学校时,我就连进食也做不到了。
那几天里,我把自己缩进了房屋,只靠喝一点清水度日。
但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悲伤、愤怒,或者别的什么心情。情绪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我只是,不解而已。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疑惑着。
我不理解为什么父母老是让我看课本,不让我画画;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喜欢玩游戏;我不理解同龄人凑一起做一些幼稚的事情就会很开心;我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朋友他们会说我恶心;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玛格丽特要对我好;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我的玛格丽特虚伪;我不理解为什么是被强奸的人失去了贞洁而没有人骂强奸者道德败坏;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五个人渣只是因为未成年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不理解为什么她要哭。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是一个变态。
我回忆着这短短几个月发生的一切,就像浸透了墨水的剧本,留给观众的只有不解。
我抱着她躺在一张床上闻着她的香味,我在不良之后强奸她。
这两个场景,至少对我来说,是过去几个月里唯一的亮色。
但我在回忆的路上只是随便的瞟了几眼就不停留地走过了,最后走到最开始的时候,我蹲下来仔细端详着。
我的玛格丽特被强奸了,然后我在没关紧的教室门外一边用手机录像一边自慰,晶莹的液体不断顺着我的腿流下来,她看着我的眼神绝望,又充满憎恨。
我清楚地记得她被强奸的每一个细节。
在那间淫靡的教室里面,男人们粗重的喘息中不时响起的她的痛呼;那些人渣趴在她身上不停地怂腰,汗水顺着她腰腹的曲线滑落在地;浑浊的液体从她的双腿之间流出来。
即使过去了这么久,再次看到这一幕,欲望的火焰仍然在我的胸膛里燃烧,让我的喉咙干涩,心脏抽疼。
于是我开始自慰,我趴在床上翘起腰,咬住右手食指,左手后伸。
先是手指绕着阴唇划动,然后拨弄了几下阴蒂,食指就很轻松的伸进了阴道里。
我的手指缓缓地转圈,感受阴道壁褶皱间的温暖。
也许是我的身体太过敏感,我的手指戳在阴道上,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在直接撕扯着我的神经。
通常,我的手指才转过几圈,我就潮喷得身后的床单湿漉无比,食指被我咬得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