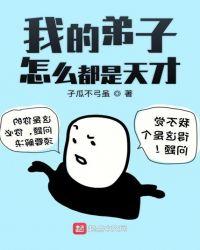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我和我的母亲(寄印传奇) > 第68章(第1页)
第68章(第1页)
父亲的关门声像骤然揭起的锅盖,使我从几近沸腾的梦中惊醒。
客厅隐隐传来奶奶的说话声。
我蹬开被子,四下摸索一通,没能找到手机。
我想瞥一眼桌上的电子表,却怎么也睁不开眼。
老二硬邦邦的,连包皮口都有点疼。
我翻个身,挠挠发痒的蛋皮,许久才喘了口气。
热。
浑身酸痛。
母亲的脚步声,她问“够了吧”,奶奶嗯了下,紧跟着是喝稀饭的声音,好一阵她老说:“……好看不好吃,你爸爸还在的时候,腌的那个才叫好。”
母亲似乎笑了笑,没言语。
奶奶喝起稀饭来恍若大型猫科动物的呜咽。
寄印传奇就在一声声催人入眠的呜咽中响了起来——我睁开眼,又迅速阖上——有个四五秒吧,母亲挂断没接,再回到座位上,她笑着说:“想吃……今年咱就自己腌点呗。”
“那可行。”奶奶说。
咀嚼食物的声音如清晨的鸟叫般细碎。
难说过了多久,昏昏沉沉中,奶奶突然提到了我。
“……林林那脸给挠的,哎——”这么说着,她压低了嗓音,于是字字句句裹挟在食物里变得愈加潮湿而闪烁,“……我说……不是招惹……哪个姑娘了吧……咋说……”后面索性变成了嘀嘀咕咕,实在不像人类的语言。
“嗐,净瞎想,”母亲笑了一下,声音随之提高了几分,“我问了,是跟几个同学闹着玩,就钢厂那个,以前来过咱家,指甲长啊——男的,男的。”
“是男的?”
母亲又是一笑。
“吓得我……唉,”奶奶连叹两声,兀地笑了起来,“男的留啥指甲,不男不女的,还挠人脸!”
母亲没说话,应该是进了厨房。
我又忍不住挠了挠蛋皮。传染般,右手伤口也开始跟着发痒。
有个半分钟吧,奶奶突然又笑开了——我清晰地听到放下筷子的声音。“哎,凤兰啊。”她说。
“再来点儿?”母亲似是回到了客厅。
“够了够了,我是说啊——”奶奶一顿,嗓音没由来地低沉下来,“剧团里的事儿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母亲没音。
“你也别嫌我烦,咱们女的啊,不能太操劳,老得快,还落一身病,那谁——老强家儿媳妇儿,在银行那个?以前跟朵花儿似的,后来当了个小官,应酬呀,喝酒呀,才几年,你看现在,四十出头,瞅着没个五十岁?”
“属啥的?”
“属……反正比和平大不了两岁,有本事的人,都没在村里住,哎——”她老的声音奇妙地消失了,跟着是啪啪两声响,一两秒的静默,“……有病,坏了!说是换,哪那么容易?你说!”
母亲轻叹口气。
“是不是……”奶奶咕哝两声,又喝上了稀饭,“女的跟男的不一样,剧团现在上了道,打交道了那些交给向东嘛,再说还有学校,对不,真要忙起来看你咋整?”
母亲嗯了声,几声脚步响,椅子的蹭地声,好半会儿她笑笑说:“那我就歇歇。”
“那可行!”奶奶也笑。片刻,一片窸窣中,她快速打了个嗝:“不用急,呆会儿林林吃完我收拾!”
没能听到母亲的声音。
好一阵,厨房里响起水声,那飞溅的水珠凉丝丝的,仿佛落在我的脸上。
又是好半晌,随着水声的消失,母亲回到了客厅。
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径直朝我的房间走来,一步步地,越来越近,直至所有声音在门口失去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