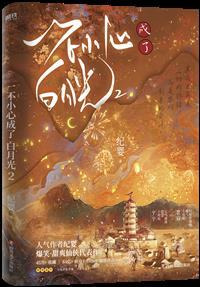墨澜小说>我和我的母亲(寄印传奇) > 第54章(第6页)
第54章(第6页)
我也不搞懂为什么要这么说,它就这么恰如其分地蹦了出来,我别无选择。
母亲扭脸瞅了我半晌,最后拎了拎包说:“乌鸦别说猪黑。”
在楼道里呆了许久我才哆哆嗦嗦地回了家。
父亲在客厅里坐着,依旧是新年诗会,至于他老有没有看进去我就说不好了。
奶奶还在屋里唠叨,说了些什么只有老天爷知道。
挨沙发坐了好一会儿,父亲才问,你妈呢。
我说不知道。
于是话语权便又让给了电视里假模假式的主持人们。
就这么呆坐一阵,他问吃啥饭。
搞不好为什么,我突然就心头火气,嚯地站起身来说:“不吃,还吃个屁饭!”
父亲仰起脸吃惊地看了我一眼。
虽然目光旋即就垂了下去,肢体却好半晌才恢复了动作——他双手下滑,在两侧裤袋上徒劳地摸了摸。
犹豫了下,我把兜里那半盒红梅给他撂了过去。
晌午闷了点咸米饭。
在我印象中,这是除了炒鸡蛋和下面条外父亲唯一会做的饭。
至于排骨和小牛肉,他说得请教请教小舅,上次学艺不精,这次还是不动为妙。
午饭奶奶倒吃得挺香,当然,免不了要听她老抱怨——“和平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干嘛老惹人生气?”
“你妈啊,脾气就是犟,我看(她)也是越长越大了。”
“打是亲骂是爱,哪有夫妻不吵架?孩儿都这么大了,别太过就行!”
饭后父亲就回了小礼庄,临走打电话叫来了护工。
三十来岁一媳妇儿,不黑不白,瘦瘦高高的,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天知道奶奶哪来那么大怨气。
我躲房间里给母亲打电话,一连好几个都是关机。
一觉醒来,她竟回了个电话过来。
或者确切说,母亲打电话搅浑了我零四年的最后一个午觉。
直截了当,她说她有事儿去林城,刚到。
具体是啥事儿,她没说,我当然也没敢问。
之后就是沉默。
良久,母亲问中午吃啥饭。
我如实回答。
她又问护工来了吧,我说嗯。
随后,母亲就挂了电话。
她说:“挂了。”
就是这样。
或许有那么一两秒,体内有种冲动驱使我说点什么,但不等话出口,字字句句便烟消云散。
而天不知啥时候阴了下来,我盯着窗外触不可及的灰影发了会儿呆,然后就打了个老嗝。
如你所料,咸米饭有点不消化。
当晚几个呆逼聚了聚,酩酊大醉。不知怎么,我们就谈起了原始森林。有呆逼说:“国际雾凇节,牛逼啊,牛逼!”
“国际雾凇节?”。王伟超哈哈大笑,火锅里的汤汤水水都要被颠得飞溅起来,“给你说,那鸡巴玩意儿啊,保不齐是拿水枪乱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