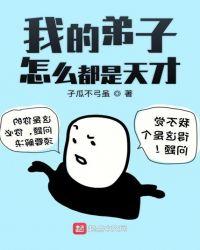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渝欢 > 2030(第16页)
2030(第16页)
他心里更加讽刺了。
打完这一下,言欢往后退开半米,隔出井水不犯河水的间距,忽而弯唇,带出一声笑。
岑寂的夜里任何细微的动静都会被放大,而她轻描淡写的一声笑,就是第三下响亮的巴掌,甩在秦执的心脏上。
他眉心紧拧,问她笑什么。
“笑你原来知道自己做了这么多荒唐又无情的事,只是一直不提,一直没有悔过而已。不仅如此,在我面前还永远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来指责我的不是。”
言欢把情绪藏得滴水不漏,话术也是,严密到毫无漏洞,生生避开了关于“现在为了一个梁沂洲”的话题。
说着,她声音忽然轻下来,对着空气重复了遍:“原来你都知道的啊。”
这几个字将秦执埋在心底的愧疚再次牵扯出来,连同他整个人一并在夜风里瑟瑟发抖,不堪一击。
言欢收敛嘲讽的神色,言归正传:“你找我做什么?为了你听到的那些真相?如果只是这样,没——”
秦执垂下眸,打断她的话:“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包括你上次找我说的那些。”
他嗓音停顿了下,似在回忆,“你说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最好的同谋……”
隔了两秒,秦执又抬起头,心猛地一跳,在对面冰冷的眼神里节节败退,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先别开眼,由着沉默持续了会,等他再次看过去,她的发丝被风吹得有些乱,他下意识抬手想替她捻开。
言欢又往后退了一步,提醒他别动手动脚的,“我已经结婚了,秦二少爷,请你自重。”
秦执手僵停在半空,捏成拳头,手背上的青筋瞬间暴起,“结婚?自重?你费尽心思嫁给梁沂洲,他就这么好?”
他完全不想把话题扯到那男人身上,但这次还是没忍住。
言欢眸光一跳,转瞬听见他递进式的话术,“好到让你单恋了这么多年,还没放下他?”
她心跳陡然漏了两拍。
秦执是在高二上学期察觉到的异常,从她某个模糊的眼神里,渐渐的,他发现,只要有梁沂洲在,她的视线总会随着他的挪动而挪动。
或许只是钦佩,不含任何男女之情。
——他这么哄骗自己,一骗就是一年多。
直到她十八岁生日那天,他提前去了秦家在外地盘下的玫瑰庄园,亲自挑选、摘下一整捆玫瑰,又特地和花店老板学了如何包装。
不仅如此,他还听了齐宵凡一回,准备好上百架无人机,打算同她告白。
但他给她发去的消息,她通通没回。
他刚心烦意乱地收起手机,远远进来一道身影,像鸟儿一般,从他世界路过。
她的裙摆很长,得提着才不会落地,但她还是跑得很快,最终在另一个人身前停下,而那人手里只拿着一支玫瑰。
隔得远,秦执看不清她的表情,但那种雀跃欢喜是不需要看的。
他的心脏骤然变成一颗柠檬,至于她的笑,就是一把把利箭,笔直地射向这颗心,汁水四溢,酸到他喉管都被溶解到红肿溃烂。
一束玫瑰和一支玫瑰的区别在哪?
为什么那单调的一枝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她所有的关注和欢喜的笑容?
后来他想明白了,有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太多,看赠予的那个人是谁。
他输就输在了那人是梁沂洲,是她喜欢的人。
“原来她喜欢梁沂洲”这个认知就像海啸一般席卷而来,将秦执的理智冲磨成嶙峋的礁石,最为锋利的那头只管狠狠扎向她,作为他被蒙在鼓里多年的报复。
他知道这很幼稚,也很愚蠢,无异于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得不到解答的困惑,时隔多年终于有了答案,言欢愣了足足几分钟,开口又是在几分钟后,“十七岁的时候,你开始疏远我,就因为长辈一句看似玩笑的婚约协定,后来我们的关系慢慢缓和下来,在我十八岁生日结束后,你突然又变了副态度,变得比以前还要刻薄、冷漠,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现在明白了,原来你是因为嫉妒。”
停顿两秒,她继续说:“处处和梁沂洲作对,哪怕只能在口舌上占他一时便宜,都会让你感到满足,也是因为嫉妒。”
“秦言两家订婚的消息正式传出后,也就是我出国后,你给自己制造一段又一段并不存在的艳遇,还是因为嫉妒。”
自己喜欢的未婚妻喜欢上的是另一个人,这让秦执体会到一种她出轨了的背叛感,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坐实自己花花公子的称号,给她难堪。
而这就是他所谓的不甘心。
言欢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尊冰冷的雕像,脚边被拉到细长的影子成了它的守护兽,两者都坚不可摧,足以击溃对面所有的防线。
她一边冷眼旁观他的狼狈,一边大发慈悲地回答了他上一个问题:“从来不是三哥太好,好到我只能选择他,而是他的好,给了我足够多选择的余地,他光是站在我身边,就构成我的底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