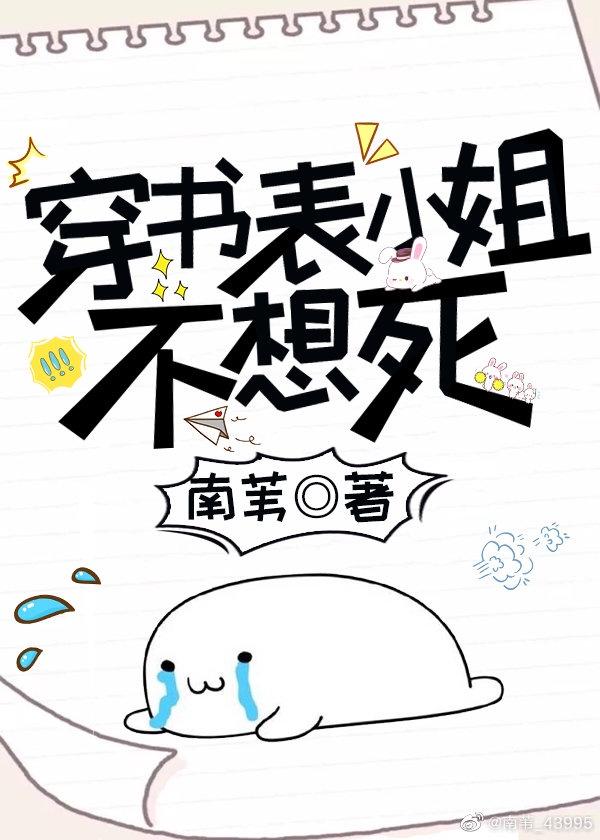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为了五险一金她决定卷入怪谈 > 第242章(第2页)
第242章(第2页)
纪云定叹了口气,有些苦恼地揉乱了自己的头发,
“就算回想以前生气的事情,也不觉得生气啊。都是些解决了的事情。”
虽然听上去很简单,但很不幸,这对于纪云定来说真的是强人所难。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努力也做不到。
渐渐的,一团乱麻的面具几乎要碰到纪云定的鼻尖,周围已经一片漆黑,只剩下了纪云定脚下的那一阶台阶。
纪云定依然低着头思索着,随后叹了口气。更严格来说,与其说是做不到,不如说是在全身心地排斥着吧。
“向内寻求答案,好吧。”
纪云定掏出了匕首,毫不犹豫地往耳内一扎,在整个世界都陷入寂静之后,她无视着近在咫尺的面具人,蹲下身,抱着膝盖,思绪飘回了另一个t闷热潮湿的夏天。
那时候,她都不知道夏天是什么,只是一个人蹲在阴暗的角落,和杂物垃圾一起。
积年累月的旧伤痕是如同手脚一般的一部分,即便纪云定在荣枯墓园忘记了经历这段记忆的感受,她的身体也还记得。
只有这件事,是纪云定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也不会遗忘的旧伤痕,是她的“情绪容器”本身。
因为在观念形成的时候,无论怎样的请求和期望都会落空,整个世界只有自己,所以无法习惯依赖他人,无法相信他人,但这样一来,纪云定依然无法抓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从出生开始打上的烙印,会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纪云定并非是在逃避,她只是不可能想明白——就像人不会质疑自己长了五根手指一样理所当然。
在过去那种环境中,失去情绪是为了保护自己,像条件反射一样。如果不直面纱布下的伤口,挑开腐烂的肉,它就永远不会愈合。
不过十几秒钟,她本能地开始自言自语,试着制造声音,如同当年在无人的储藏室中一样,试着制造些响动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还存在。
但现在,她什么都听不见。
寂静中,纪云定闭着眼睛,感受着本能的恐惧,同时如同旁观者一般逐渐产生了“愤怒”的情绪。
愤怒这种情绪比其他情绪更好解释,所有愤怒的原因说到底不过三个字——“凭什么”。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周围仍然一片漆黑,但纪云定看到一道不知来处的反光一闪而过。她立刻向那个方向伸手,攥住了剪刀的尖端。
抓到你了。
显然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角力,但只要纪云定一松手,这把剪刀一定会立刻隐去。好在,纪云定现在真的很生气。
“给我,这个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