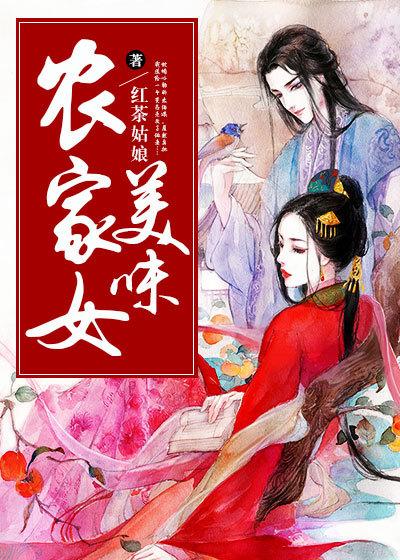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鲛人反派有点撩[重生] > 第150章(第1页)
第150章(第1页)
就在他转身之际,浓长的睫毛动了动,转瞬即逝。关好了窗,杜引之又迫不及待地钻进被子里,将小叔再次搂入怀中,眉头微蹙,或许是天气变暖了,小叔的身体也不似先前那般冰冷,抱在怀里温润似软玉。在眉间轻轻落了个吻,保持着嘴唇紧贴额头的姿态,心满意足地入睡。“小叔,明儿你就醒了罢?”每天临睡前他都要重复一遍这句话,语气是小心翼翼的撒娇,总觉得这般死皮赖脸的祈求,小叔定然舍不得抛下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小时候他无数次幻想,小叔能这般乖乖的任他抱着睡,从日沉睡到月落,又从日出睡到月升,再也不用理会旁的事,只沉沦于彼此的气息体温就好。现在这样,已经很奢侈了,只小叔再不会与他说话,不会责骂他,不会叫他引之叫他小鱼儿,只余几缕残魂在空荡荡的身体里游荡……“小叔,你若醒来,可要好好与侄儿说一会儿话啊,把这三个多月的份都说了,我才原谅你的自作主张。”“我虽对你百依百顺,也是有脾气的,这次我是真生气了。”“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怎么可以擅自做出那种事呢?”“要好好惩罚才行。”低低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梦呓,屋外风吹竹动簌簌而响,虽然生气,他仍是舍不得与小叔说重话。那日,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如何抱着失去意识的小叔从狂骨教的废墟中爬出来的,胡乱用外袍遮住两人的身体,整个人都混混沌沌,身上被碎石划出无数道血口子,鲜血混着尘土流淌而下,双目赤红,身上颤抖不止,狼狈不堪面无人色。直到有一人截了他的去路,是柏旭。他记不清当时柏旭是什么表情,杜引之的五感都消失了,看不见,听不见,柏旭一剑刺入他的胸口,晦暗的眸子才稍稍有了些反应。胸口处一阵锥心的疼,他微微低眸,看到没入胸口处的剑,怔愣了片刻,默然抬起手握住剑刃,生生拔出,锋利的剑在他血肉模糊的手中瞬间化为齑粉。鲜血从被刺穿的胸口喷涌而出,杜引之浑不在意,似坏掉的木偶般死死盯着怀中双目紧闭的小叔,直到鲜血溅到小叔的鬓角,他才抬起手仔仔细细的抹掉。小叔爱干净,不能让自己的血弄脏他——“把言疏给我!”望着杜引之怀中衣衫不整面色苍白的杜言疏,柏旭双目赤红,声音发颤,胸口剧烈起伏,正是一副对杜引之恨之入骨的形容。暗淡的眼眸闪了闪,将怀中毫无知觉的人抱得更紧了,声音缥缈似梦呓:“小叔是我的。”“畜生,你也配?”“三番四次将言疏置于危险境地,这回终于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了罢?”“言疏他,终究还是为你而死。”杜引之的身子猛然一颤,声音低低的游曳在血腥弥漫的空气里:“小叔他没有死……”“杜引之,把他给我!”柏旭没了剑,赤手空拳更是靠近不了半分,现在对杜引之而言,没有什么比怀中这人更重要了,他如何会舍得让给旁人。即使只是一具空荡荡没有神魂的肉体,那也是小叔……“给我,我有办法——”漆黑的眸子定定的看向杜引之。“虽不敢保证,却值得一试。”语气笃定沉冷杜引之身子颤了颤,眼神终于有了些许焦距,神色复杂地望向柏旭。柏旭嘴角抽了抽,一字一字道:“血绊。”他与杜言疏之间,血绊还在,虽然没有把握,不妨一试——用他的命,换言疏的命。无论对方是他心心念念的三爷,还是血浓于水的弟弟,他都义无反顾。杜引之忘了自己是如何鬼使神差将小叔的身体交给柏旭的,只记得一阵耀目的光团炸裂开来,照亮整个狂骨教的废墟,烟尘四起,久久未能消弭。“这次,便宜你小子了。”“三爷……我弟弟……就拜托你了……混账……”说完这句话,那张永远不苟言笑的脸浮起一丝自嘲的笑,眸子中的光彩一分分褪去,最后那团火焰,熄灭了。漆黑的眸子是睁着的,杜引之抬手为他合上眼皮,重新将小叔抱在怀里,珍重的,小心翼翼。莫渊山隐匿在东域须臾之境,山中风水极佳,灵雾缭绕,神木参天,翠竹掩掩,最是适合修复神魂灵脉,只莫渊山入口极难寻觅,据说百年来无一人找到过。杜引之背着毫无知觉的小叔,只用了两日便抵达极东须臾之境,又花了两日踏遍须臾之境每一寸土地,终觅得莫渊山入口。即使灵力充沛如他,也因消耗过大重伤在身昏迷了一日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