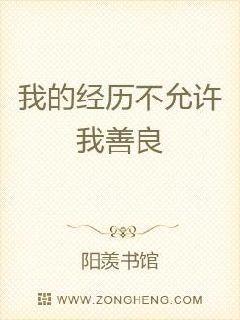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在没有女人的春秋战国里 > 第289章(第1页)
第289章(第1页)
经过寺人射这么一解释,他的徒弟,那个年轻的寺人也明白了其中分晓,道:“原来如此,徒弟受教了。”
寺人射仰天长叹一声,对那年轻的徒弟道:“乖徒儿,你只需记住,这宫中内位之主,除了国俌,其实在君上心中都只是……”
后面的话,言未尽,意无穷。
从南方向北前往无终城的路上,一骑快马飞奔进城,然后,很快的,主理情报的斥候将军急急入宫觐见国君,开口第一句就是:“禀报君上,晋军攻齐!”
服人一听这个回报,几乎是将案几差点掀翻的力度突地站起,一把抓住斥候将军的衣领,道:“当真!?”
而处理完那抱回自己正室寝殿的小婴儿时,夏瑜突地神色一动,望向南方,不自禁的喃喃自语道:“机会来了?”
☆、
“国俌到!”
国君寝殿外,寺人大声通报着。
完全无视寺人尖厉的嗓音,夏瑜带领着一众心腹朝臣步履略有焦急的快速步入殿中,见服人已经与朝臣武官与武卫军士围在沙盘附近,在紧张推演,朝臣也好武卫军士也好,见到夏瑜进殿都急急行礼,夏瑜却很是不耐的一挥手,道:“不用多礼!”
没有半分耽搁,夏瑜急急行至服人身侧,道:“君上如何看法?”
服人一直皱着眉头看着那沙盘上齐国与晋国交界的地方,道:“不太对劲儿,晋国的誓师大会已经开完了,国内也在动员,可是大军调度却是异常缓慢。”
夏瑜看着沙盘,上面摆放着象征着晋军的小军旗和象征着齐军的军旗,眼看这进军位置,他也是早就知道的,只是此时想与讨论下燕国的应对,毕竟这是一个太过难得的机会,道:“当年攻打中山国时,智氏与赵氏合作尚且无隙,虽然中山国在首辅公孙启主政下,施以奇谋,留下空城给晋国,又暗中联络赤狄潞氏,半途偷袭,但也因为智氏与赵氏配合无间,稳住阵脚后殊死反扑,赤狄并没占到什么便宜。”
服人点头,道:“那个时候赵氏与智氏,能够看出来尚且无嫌隙,可是三年后攻郑国,赵无恤便不服从智瑶调遣,再三年后晋国再次攻卫,晋国四卿齐出,智瑶与赵无恤各自领军,韩氏、魏氏各自领军,如此看来,倒是赵氏与智氏嫌隙日渐加深?这次出兵缓慢也是因为晋国内政不协?晋国公卿内斗又起?”
夏瑜心中倒是有几分知晓内情,但此时却不便直言,便道:“斥候如何回报?”
服人道:“尚未有消息回……”
就在此时,只听殿外一声气喘吁吁的声音喊道:“报!!!晋国军报!!!”
服人一愣,他曾亲自下令,但凡军报,不用通报,可以直接入殿禀报,此时只听那斥候将军飞奔进了殿中,因为跑得太快,脚下竟是有些踉跄,奔至服人身前不远处,正要行礼,却被服人一挥手,道:“不用行礼了!军报呢!?”
那斥候将军将手中军报呈报给服人,一边呈报纸上军报,一边口里汇报道:“晋军动了,这词智氏与赵氏又是混编。”
自从夏瑜推广了纸张的应用,发布法令将朝堂奏章都改用纸张上奏,军中军报也渐渐改为纸张呈报,这也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燕国的奏章也好军报也好都比往昔的字数更多,也更加详尽,毕竟用竹简能记录的字数和一大块宣纸能记录的字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服人接过纸质军报,细细阅读,然后神色间便有了几分不解,道:“这次智氏与赵氏又是混编?这两家和好了?这……嫌隙渐深,却能转瞬就和好,相互托付后背生死与共?这可能吗?”
夏瑜听到这话,淡淡道:“情之一字,从来莫测,有情人之间,可能会有争吵,也可能转瞬和好,并不稀奇。”
听到这话,服人一愣,然后转瞬间似乎明白了什么,道:“你是说赵无恤与智瑶之间是……”后面的话服人没出口,似是有所触动,服人微微沉默,顿了一下,接着道,“无论如何,只要晋国能够抱成团来攻打齐国,不要再因为内乱而耽搁外战,于我燕国而言就是好事。”
说道此处,服人转头望向大殿里挂得那副四海归一图,目中有些回忆之色,不自禁的道:“阿瑜,我燕国……我们迁国多少年了?”
听得此问,夏瑜神色也有了几分回忆的惘然,低声道:“到今年正好满十五载。”
服人微微长吸了一口气,道:“十五载啊,有些迁国之后出声的小伙子,都不知道燕国故地的山河是何模样了”,说到这里,转头看向夏瑜身后的公子谦,眼中也有些感慨之意,道,“连谦儿都快要到加冠的年纪了。”
听到提及自己,跟在夏瑜身后的公子谦出列向服人行礼。
服人看着公子谦,目光中有了点温和还夹在着点愧疚的神色,道:“谦儿还有多久就要行冠礼了?”
公子谦本来是十分乖巧聪敏的性子,但是自从六年前经历过无终城终的那场大瘟疫,被自己的公父下令与几个换了瘟疫的弟弟一起被锁在一处内院里,眼见着几个弟弟一一病死,不知道是不是刺激太过,其后虽然好转痊愈,竟是变得很是木讷,此时听得君父有问,只是讷讷回道:“还有三载。”
服人目中愧疚之色更胜,点了点头,便不愿与公子谦再交谈下去,转头对夏瑜道:“出使晋国的使者有消息传回来吗?”
夏瑜眼见服人与公子谦寥寥数语,又想起那几个死在瘟疫里的孩子,大的不过四岁,小的刚满周岁,小小的身体被浇上石灰就地火烧入殓时,他这个不是血缘亲人的都觉得不忍,何况亲父,方木当时一看见这一幕就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