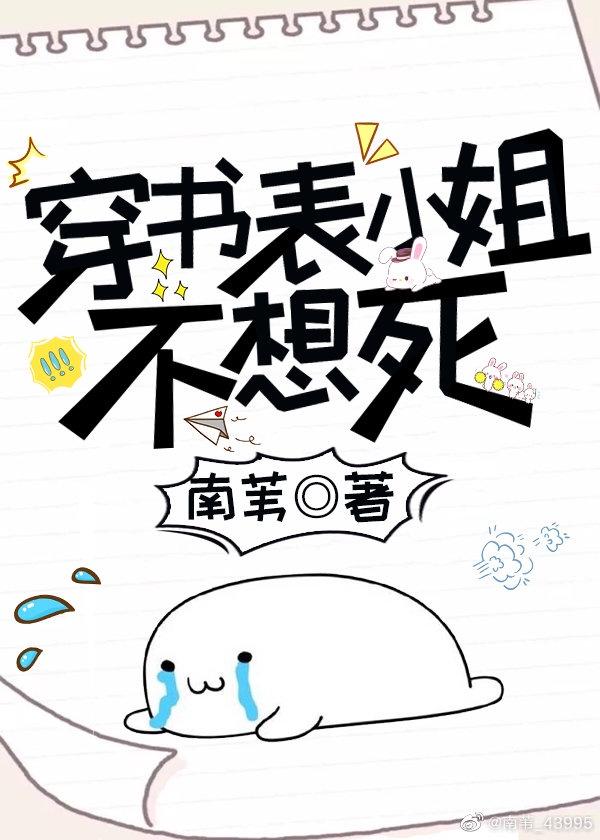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情深深雨蒙蒙同人)重生陆如萍 > 第136章(第1页)
第136章(第1页)
而且这个小妞可是看清楚了他们长什么样子,最后若是不处理了她,他们从此就真要逃亡去。多做少做能有什么区别?光头想着,对着依萍那张如花似玉的脸猥琐一笑,依萍正好看过来,恨恨地移开眼。
秦五爷曾经是黑道出身,自从做起了歌舞厅的生意之后,渐渐就由黑转白。他现在在黑帮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却再也不肯做违法的买卖。所以绑架,就算是假的,若是被捅了出去,也是不小的罪名,于他的名声和产业都有损,偈他这样小心翼翼的人怎么会干那种蠢事!
他答应了依萍后,就找来了别人,所以才出现了这种不在控制范围内的情况发生。他本以为这只是小事一桩,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是帮着小俩口搓合搓合感情罢了,他又卖了人情,又和白玫瑰签下三年的约,是稳赚不陪的生意。
晚上时,那四个人中有两个走了,看他们那悠闲的样子,不像是去放风,而是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乐子去了。
只留两个人看着依萍,其实她也不用人看着,手脚和嘴都被封得牢牢的,又在最里面的角落里,以她现在的状态想要逃跑,就算用一个晚的时间,她也挪不到门口那里。
所以依萍也没想着跑路,而是又饿又累地窝在墙角里睡觉,老三还好心地给了她一张旧毯子,要不然非感冒不可。
依萍睡得迷迷糊糊时,感觉有人在摸她,她想起现在的处境,顿时如兜头一盆凉水泼下,瞬间清醒过来。她身边果然有个人,借着微弱的煤油灯,能看到那颗发亮到让她恶寒的光头,光头此时正在她的身上摸来摸去呢,他那满是脏污的手甚至探进了她的衣襟里!
依萍眼睛瞪得老大,她拼命的扭动起来,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想挣开他,却发现用上全身的力气,她几乎没有移动,光头却看笑话般地看着她在做无用功,而且对她的扭动更兴奋了,他的动作越来越大。
依萍内心极度慌乱,她怕极了,就在她要绝望之际,她的脚踢到了杂乱放着的水壶,‘哐当’一声响,光头沉迷的动作一顿,也惊醒了不远处睡着的老三。
老三半夜里被惊醒,差点看到活春宫,气得跳脚:“他妈的,光头你有完没完!老子说了多少遍,这个女人碰不得,你有火气就跟着瘦子他们去醉春楼!在这儿折腾什么!”
光头好事被打断,相当懊恼,也骂骂咧咧了几句,还不解气地踹了依萍一脚,不过他到底没有继续下去。现在他们还以老三为头儿,大小事情都是老三说了就算。
若还是白天的依萍,一定恨不得他们窝里斗打起来,可是现在她可不敢想,她的心脏正以不正常的频率‘砰砰砰’地跳着。
过了一会儿,那两人都骂累了,躺在木板床上打起呼噜来。依萍不敢睡,她直直地盯着那边的人,睁着眼睛到天亮,其间光头每次翻身,都能把她吓个半死。她这时才真正明白,外人的恶意和身边的家人朋友比起来,简直差得太多太多了。
她爸再不爽她,最多拿鞭子抽她一顿,事后还总想着示好弥补;她妈嘴里说着,让她不要再折腾,每当她半夜睡不着,出门夜游的时候,她妈总是披着件单衣,几步外面跟着她,赶都赶不走;书桓……他虽然气她,最多说几句重话让她伤心,根本舍不得对她动手。
这一刻,依萍后悔极了,后悔听信了外人的话,害自己陷入如此境地,她决定,若是她能平安出去,她以后都会乖乖的,她会收敛她身上所有的刺,他们说什么她都听,不会再一意孤行了。
绥远市西南方,离战场的不远处,是中队的驻地,又一场小规模战役过后,战士们带着伤兵回营地。医疗站是军用的大帐篷临时搭建起来的,轻者住在里面就好,重者做了初步处理之后,就转到后方相对稳定的医院里去。
现在的医疗站里面热热闹闹人声鼎沸,战士们的呻吟呼痛声,医生护士的吆喝叮嘱声汇成一片。何书桓此时正躺在一张军用的床上,胳膊上缠着绷带。他这是在上一场战斗中,为了救一个孩子而负的伤,并不严重,只被子弹擦过,在胳膊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不过要处理消炎,所以耽误了他回报社的时间。
军团的团长都夸他奋勇当先,只是要下不为例了,没有武器的记者,最好不要再冲到前面。可是事情如果再重来一次,何书桓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冲出去。
这样热血战场上的日子,他总是不怕死地跑到最前线的敌人对面,事实报导,记录这场战争。儿女私情在这样的家国天下面前,就变得极其渺小,他很少再想起依萍,有时忙得太累了,恨不得躺在地上就能睡得着,更是几天几天地想不起她来。他喜欢这样充实的日子,让他不再混乱,可是现在他受了伤,闲下来,躺在床上又有大把时间胡思乱想了,他要找点什么事转移注意力,不然纠结的脑袋是要发疯的。
这时,一个大眼睛的护士走到何书桓病床前,她这一身纯白的护士装,就算在离战场这么近的地方,也能保持干净整洁。她对他扬起一抹甜蜜的笑容:“书桓,该换盐水了!”
何书桓本来在床上发呆,看到是她,也露出一个微笑:“麻烦你了,汪护士。”那护士横了他一眼,眼神里有说不出的娇嗔:“我都已经叫你的名字了,你还叫我汪护士?”何书桓笑了笑:“好吧,麻烦你了娉婷,这下你满意了吧!”
说来也巧,这个汪娉婷跟他还有些关系,他们的父亲竟然是同事,同在南京政府工作。两个年轻人又能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相遇,这不就是缘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