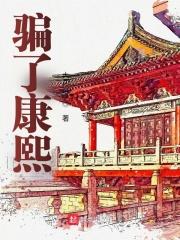墨澜小说>遇惹生菲(1V1SC高H) > 干红(第1页)
干红(第1页)
手上的罗曼尼康帝刚刚被从低温的酒柜里拿出,上面还裹着一层薄薄的保鲜膜,以保护它容易发霉的标签。
裴菲菲轻轻放下酒瓶,切开酒帽,将醒酒器和ah-开瓶器从酒边柜拿出。
这可是一瓶年份比她还大的酒了,尽管不能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酒比,但软木塞已经被泡得有点不行了,用一般的开瓶器容易出现堵塞的现象。
她仔细地把ah-两边长短不一的脚固定在软木塞两旁,而后用巧劲左右摇摆,不出一会就顺利地把木塞拔了出来。
别看裴菲菲是个妥妥的精神病人,她从小就过得锦衣玉食的,也算是骄奢淫逸的主。
哪怕是后来被父母打包带走了京城,十年如一日过着被人pua和嫌弃的日子。
这些品酒的门道,由于儿时的好奇,再加上后来得病治疗,老太太多少次陪她国外散心,早就在她心里娴熟无比。
doaederoanéenti
被大众称为天价的美酒,她喝过不下几十次,可是却尝不出什么滋味来,每次都当作伴牛排的饮料喝,总被熟悉的侍酒师调笑是“牛嚼牡丹”。
她每次都摇摇头,无奈地笑,老太太不喝酒,饭桌上没有人陪她,喝再好的酒,也只是她一个人的寂寞与孤单。
可这次好像不太一样,她第一次这么想把平时喝的酒分享给另一个人,想喝次不寂寞的酒。
这和同奶奶分享不一样,和奶奶在一起,裴菲菲觉得很安心、幸福;可是和他在一起,她觉得她可以做自己,特别、特别自由。
她打开手机手电筒,照着酒瓶,以免酒渣掉落,小心地把酒注入醒酒器。
酒的颜色清透明亮,是不那么深沉的红。
等到宋蕴生吹完头发出来,就看到裴菲菲盯着桌子上的两个酒杯,杯子里的红色葡萄酒随着光的折射而泛出美丽的色泽。
“你来啦~”裴菲菲转头看他,展开怀抱。
“突然想喝酒了吗?”宋蕴生迎着她的抱抱,把脸微靠在她的肩头,“还是这么贵的酒。”
“对,roanéenti,干红。”
“你会法语吗?宝宝。”
“会一些,我之前在法国散了两年半的心。”
“jet’aiàfolie”
宋蕴生看她喝酒喝的红扑扑的小脸蛋,不禁想起之前交换时法国同学教他的法语发音,他练了好多遍,去她的墓碑前说了好几遍。
“发音还行,不过重音错了~”
“jet’aiasi~”
她摸摸他的头,递给他一杯小满的酒,“你喝杯大的,我就告诉你什么意思~”
他乖乖喝下,几乎一饮而尽,酒液的香气顺着喉管滑过,随之而来的是单宁的涩苦和黑皮诺的香甜,让他有些迟钝的快感。
“这么乖,是我、也、爱、你的意思哦~”
裴菲菲抓开男人身上的浴袍,接着抬手吞进一大口酒,再和他接吻,用自己小巧挺翘的鼻子蹭他的鼻梁,用酒一遍遍浸润他温热的唇,一边含糊地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