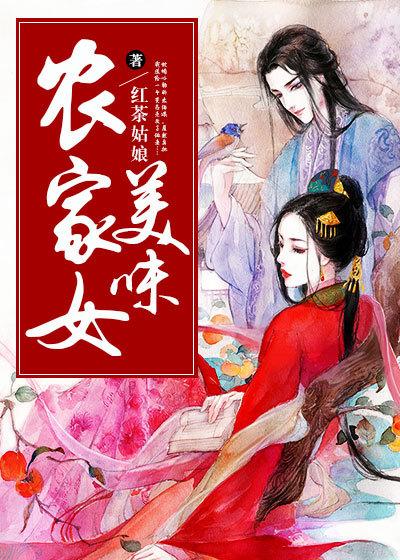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奸臣他又美又癫 > 分卷阅读20(第1页)
分卷阅读20(第1页)
……和太宰睡了!”屠怀信:“……”屠怀信被吵醒,眯起眼目,一把捏住屠怀佳的脖颈,将人拽过来,让屠怀佳面对着自己。“哥哥?”屠怀佳一脸迷茫:“你、你怎么在这里?太宰呢?”屠怀信的脸色黑沉沉的,沙哑的道:“太宰自然在太宰的帐中下榻。”“啊?”屠怀佳更是一脸迷茫,脸色出现了短暂的空白,眼珠子微微转动,紧跟着转动的速度变快、更快、飞快!“我……你?!”屠怀佳指着屠怀信,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这一瞪眼,他清晰的看到屠怀信的脖颈上攀附着几枚新鲜暧昧的吻痕,那是……自己留下的。屠怀信沙哑的道:“想起来了?”屠怀佳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道:“我、我们……昨天晚上,是你?”嘭!一声闷响,屠怀佳因着太震惊了,向后错了好几下,一个不慎跌下软榻,摔了个结结实实。屠怀信无奈的看着毛手毛脚的弟弟,弯腰将屠怀佳一把抱起来,轻轻放在榻上。屠怀佳浑身僵硬,他感受着屠怀信温暖的怀抱,这微妙的温度,微妙的触感,真的和昨日醉酒之后的缠绵一模一样!屠怀佳羞耻的紧紧闭着眼睛,心跳飞快,心窍震得发酥,脑海中一片空白,舌尖仿佛打了结子,根本不知如何开口。屠怀信看着他满脸通红,死死闭着眼睛的模样,忍不住在他耳畔轻声道:“佳儿昨日不是说要与我算账么?”“算……算账?”屠怀佳迷茫的睁开眼目,对上屠怀信一成不变的冷酷脸面,但那双死水一般的眼眸中,此时此刻却略微充斥着一丝调侃。屠怀信道:“你昨日说,早就发现哥哥偷亲于你,要与我算账,现在不算了?”屠怀佳怔愣,脑海快速旋转,是了,他上次就发现了,屠怀信偷亲自己,但屠怀佳没有胆子挑明,也不知为何自己没有胆子,或许因着自己是屠氏的冒牌货,也或许是其他甚么不可明说的缘故……“我……”屠怀佳语塞,张了张嘴唇,只觉得喉咙干涩,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屠怀信幽幽的看着他,眼神愈发的深沉,仿佛食人的野兽,突然双手撑在榻上,将屠怀佳圈在怀中,低头含住屠怀佳的嘴唇。屠怀佳轻哼了一声,手足无措,想要推开对方,指尖触碰到屠怀信的胸膛,狠狠打了一个抖,一时舍不得,一时又不敢,如此反复。“屠将军。”营帐之外传来声音。屠怀佳吓得狠狠哆嗦了好几下,脱力的瘫软在榻上,胸口急促的起伏喘息着。屠怀信微微蹙眉,似乎因着被打断有些不悦。来人道:“屠将军,陛下请屠将军前去议事。”屠怀信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吐息,道:“知晓了,这便过去。”屠怀信垂头看着小可怜一样软在榻上的弟弟,眯了眯眼目,将旁边的锦被拽过来,给他仔细盖上,轻声道:“困倦便再歇一会儿,哥哥先去谒见陛下。”说罢,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屠怀信穿戴整齐,换上一身肃杀的黑色戎装,转身离开了营帐……“卑将拜见陛下。”屠怀信进入御营大帐,跪在地上作礼。御营大帐之中,梁错和刘非都在,因着刘非中毒虚弱的缘故,此时坐在席上,靠着铺了软垫的凭几。
屠怀信并没有多问,他素来便不是喜欢好奇的性子,只是恭敬的道:“不知陛下有何吩咐。”梁错意义不明的笑了一声,道:“怀信昨夜歇得可好?”屠怀信眼眸微动,还是恭敬的回答道:“谢陛下关怀,卑将诚惶诚恐。”梁错并没有深究,而是道:“太宰发现了南赵在暗地里使绊子,欲图在猎犬之上下毒,毒害朕与大梁的臣工。”屠怀信抬头看了一眼梁错,眼神中略微有些惊讶,用猎犬动手脚?今日便是夏苗之日,不只是大梁的人主梁错,但凡是有头有脸的臣子,都会为了彰显大梁的国威,尽力狩猎,届时所有参加夏苗的臣工,无一例外都会中毒。猎犬……屠怀信心动今日是夏苗的日子,大梁的臣工们,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早早换上了狩猎的劲装,来到营地的空场,成群的攀谈。徐子期昨日被打了脸,脸上全都是青紫的血道子,他今日特意戴了帷帽,遮住自己的面孔。“诶徐大夫,”有好事的臣工奇怪的道:“今日狩猎,你如何戴着帷帽?一会子如何能尽兴狩猎啊?”徐子期干笑道:“风沙太大,我有些水土不服。”众人调侃道:“徐大夫这样的文臣,又是徐州有名的美男子,与咱们这些大老粗便是不一样的。”刘非从营帐走出来,便听到众人的谈笑之声,大家虽觉得徐子期奇怪,但也没有强求他摘下帷帽,刘非挑了挑眉,不得不说,他这个人是记仇的。刘非走过去,状似不经意,“嘭!”狠狠撞了一下徐子期的肩膀。“哎呦——”徐子期往前一扑,撞在营地的牙旗柱子上,撞得不算太恨,但头上的帷帽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哎!”臣工们立刻惊叫出来:“徐大夫,你的脸?!”徐子期刚扯谎说自己水土不服,如今脸上青青紫紫的痕迹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