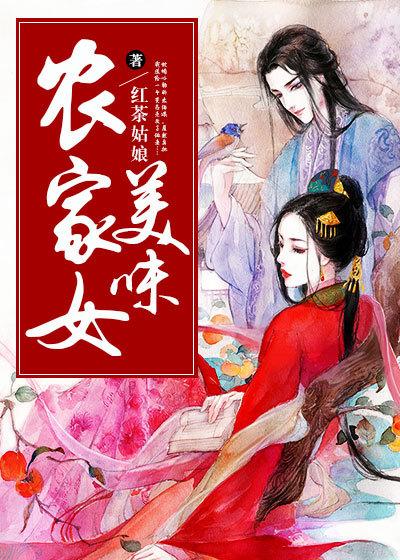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野蛮娘子想杀我!重生踏上修真路 > 第370章 装病(第2页)
第370章 装病(第2页)
言罢,他昂首对传讯军兵吩咐道:“请迟先生至我卧房一叙。”
“将军……”谋士们欲再劝,却被方全以手势制止,斩钉截铁道:“照我吩咐行事。”
当军兵引领迟勋步入方全的卧房时,只见方全已病弱不堪,慵懒地倚卧于床榻之上。
四周,一众将士恭敬地跪坐,神色凝重。
迟勋风尘仆仆自圣罗城赶来,脸上尚挂着旅途的疲惫与尘土。
他步入室内,众将士纷纷起身,拱手齐声道:“迟先生。”
迟勋目光扫过众人,回以礼数,随即聚焦于病榻上的方全,关切询问:“闻听方兄贵体欠安,不知病势如何?”
言罢,方全勉强抬手,声音微弱,似风中残烛:“可是迟老弟到了?”
迟勋趋步至床前,细观之下,只见方全面色惨白如纸,唇色青紫,一副病入膏肓之态。
迟勋心中是既生气又好笑,方全自称水土不服,此刻却装出一副病重的模样,到底是想闹哪样?
他暗暗摇头,还是蹲下身来,温言问道:“方兄,我特来探望,却见你病势如此沉重,实非水土不服所能解释啊?”
方全苦笑,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唉,自踏入东关这方水土,我便厄运连连,疾病缠身。迟老弟此番前来,莫非仅是探望之情?”
迟勋闻言,神色坚定:“探望之情自然是有,但更重要的是,我欲邀方兄共赴圣罗城,与大人举天同庆。”
方全微微眨眼,刻意清了清嗓子,略显夸张咳嗽道:“迟老弟,眼下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大人盛情相邀,我本应欣然赴约,怎奈这身躯竟如此不争气,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长途跋涉,难以胜任啊!”
“确实如此,将军病势沉重,此刻前往圣罗城,途中恐有不测,还望迟先生能在大人面前代为转圜,详尽阐述将军的实情。”众谋士纷纷附和,言辞恳切。
迟勋闻言,轻轻颔首,自怀中取出一方洁白手帕,悠然自得地擦拭着手掌,随后神色凝重地说:“方兄,我虽非名医,却也略通医术。让我为你诊一诊脉,那些疑难杂症我或许束手无策,但对于水土不服这类小恙,我自信尚能应对自如。”
言罢,他卷起衣袖,作势欲探,方全见状,下意识地往回一缩手臂,脸上挂着几分尴尬的笑意:“哎呀,迟老弟,不必麻烦了,医官已为我诊断过,只需静养半月,自能康复如初。”
迟勋闻言,眉头微蹙,一本正经地道:“区区水土不服,竟需半月方能痊愈,此等医术,岂非庸医所为?”
他语气坚定,继续说道:“方兄放心,此等小疾,我半日之内定能使之痊愈。”
方全闻言,苦笑不已,深深凝视迟勋一眼,见他态度坚决,非把脉不可,索性不再掩饰,从床榻上坐起身来,笑问道:“老弟,你这是看出我在演戏了吧?”
他语气中既有无奈,又带着几分对迟勋敏锐洞察力的钦佩。
迟勋嘴角轻扬,优雅起身,向方全挥手笑道:“方兄,快请起吧,您这身板硬朗如松,卧床装病岂不委屈?”
方全朗声大笑,笑声中夹杂着一丝尴尬。
他轻扬手,示意侍立一旁的丫鬟,后者轻盈上前,递上湿漉漉的手巾。
方全接过,随意拂面,顷刻间,脸颊泛起自然红晕,神采奕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