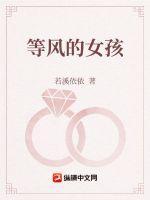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冷王嗜宠:我家王妃初养成+番外 > 第468章(第1页)
第468章(第1页)
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另外一个人,兮萝,也混迹在了其中,因为她的穿着打扮便跟那些黑衣人一般无二,混迹其中,也是无人认得出来。而此时的隐族,原本是一处山明水秀,景色靓丽之所,但是此时,却是横尸遍野,鲜血横流。便是连原本围绕山头的鸟儿,也似是被这一番血腥场景吓到了,离得远远的,丝毫不敢靠近。他们一行人回到族里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场景。柳纪年和柳桃之的脸色一下就变了,面色煞白,柳桃之险些直接晕倒在地,浑身都在颤抖。怎么会这样?事情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他们身后一众黑衣人,也都纷纷腿软,再也顾不得其他,四散着朝着自己家里的方向而去。柳桃之强忍着眼中的泪,亦是朝着自己家里的方向而去。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爹!爹!”然而,待她跑到家中,看到那个倒在血泊中,气息全无浑身冰冷的尸身时,所有的呼唤都梗在了喉间。她扑了上去,眼泪簌簌地流,抱起地上的人哭喊不止,“爹!您快醒醒啊!快告诉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爹……”然而,不管她怎么哭喊,怎么叫闹,地上的人都已经彻底睡着了,没有给她半分回应。柳桃之哭得眼睛都肿成了核桃,半晌,她才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了怀中的人,趔趄起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她跑得很快,穿过了一排排房屋,最后跑到了后山的方向,在那后山中七拐八弯避过了一个个机关,终于到了后山,那里赫然有一间小竹屋。柳桃之站在竹屋面前,脸上的泪珠晶莹,她的脚步却是生生顿住,半晌都不敢迈出那一步。她嘴里喃喃,“屋外的机关尚好,姨母一定没事,一定没事的!”柳桃之嘴里喃喃低语着,可是还没来得及抬步,忽地,便有一道黑色的影子飞快地蹿了进去,柳桃之惊疑之时,还没看清,紧接着,另外一道影子又蹿了进去。柳桃之只觉得那身影颇为眼熟,她当即便也不敢耽误,快步跑进了竹屋。刚破门而入,看到眼前的情形便不自觉呆了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这竹屋里突然出现的那两个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人:慕容北辰和慕容兮萝!慕容兮萝穿着一身的黑衣,那装扮便方才的黑衣人并无二致,想来她便是这么跟着混进来的。而慕容北辰,依旧是方才的那身装扮,只是,他竟然从一开始就跟着他们,他们竟然也毫无察觉?柳桃之现在根本无暇去想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问题,而是神情僵硬地看着同样倒在地上的美貌妇人。她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血染红了她身上的白衣,已经凝固,整个竹屋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兮萝跌坐在地上,眼中含着晶莹的水光,却是没让那泪珠落下来。兮萝抱起了地上的妇人,手有些颤抖地伸向了她的脸,摸着那冰凉的面颊。这张脸,落在兮萝的眼里,虽然原本脑中半点记忆也无,但是这一刻,却像是心有灵犀一般,一下就让兮萝的心跟着颤了起来。她知道,就是这个人,她的娘亲,就是这个人!兮萝的身子都禁不住一阵阵颤抖,眼中的泪珠终于是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无声地哭着,那模样,光是瞧着,便已是叫人觉得心里发疼。慕容北辰站在旁边,整张脸都背着光,隐匿在其中,叫人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但是,他周身间,却释放着一股叫人觉得胆寒的冷气。兮萝的眼泪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忽地,那个被她抱在怀里的妇人眼睫颤了颤,片刻之后,她颤颤巍巍地睁开了眼睛,掀开了一条缝。兮萝泪眼朦胧中,惊得失了方寸,就这么望着她,连哭都忘了。黎氏睁开了眼睛,视线半晌才缓缓聚焦,在看到兮萝的一瞬,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大,其中有光彩一点点绽放。柳桃之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腕,给她把脉。她还活着,那便还有一线生机。可是,刚把上去,探清楚她的脉搏,柳桃之心底生出的那一丝希望便一下熄灭了。没希望了,那一刀伤到肺腑,身上更有更严重的内伤。柳桃之捂着脸无声地哭,她抹了一把泪,哽咽着道:“姨母,瞧我把谁带回来了?这是兮萝表姐,还有北辰表哥,他们都来了,都来看您来了!”柳桃之一把粗暴地把慕容北辰一扯,便把人扯到了黎氏的面前。而慕容北辰的脸,一直绷得紧紧的,目光幽沉,面无表情,不知在想些什么。黎氏的目光痴痴的,看着兮萝,又看着慕容北辰,像是在看这世间最珍贵的珍宝,她的眼角很快便划过了一滴晶莹的泪。她竭尽所能,张嘴,声音低若蚊蝇,“娘的好孩子,好,好好的……”她说完这句话,那强自撑开的眼皮,便在这一刻,彻底地合上……往事一瞬间,原本就安静的竹屋变得更加安静了。因为这样的安静,其他的感官便越发强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越发汹涌,强烈地刺激着在场三人的鼻息。兮萝最先反应过来,哇地一声就大哭了起来,眼泪簌簌地往下落,滴答滴答,落在人的耳里,平白就叫人觉得心里狠狠地揪在了一起,整颗心都跟着发酸。柳桃之的眼泪也是不停地往下落,难以自抑的难过。姨母虽不是母亲,这些年,在她们姐妹心里,却是充当着母亲的角色,照顾她们,陪伴她们。可是现在……慕容北辰的心里像是忽然空了下去,原本所有的情绪似乎都在这一刻被抽空,整个人都有一瞬间的茫然和空白。他面容紧绷,眼眶中隐隐有异样的情绪在翻涌,然而,他却没有让自己情绪外露半分。他有些木然地起身,抬步在竹屋里走着,看着这小小屋子里,简单的陈设。每一样都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物什,可是目光所及,他却仿若能轻易地联想到她再这里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音容笑貌。他的目光忽而落在了一个妆奁匣子上,那是一个颇有年头的匣子,上面的缠枝雕花都已经磨损,看不清本来的雕工。似心有所感,他伸手,打开了那个匣子。看到里面的东西,慕容北辰的眼睛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原本就干涩得厉害的眼眸被刺激得更涩得厉害。那里面放着的几个小玩意儿,最上面的,是个拨浪鼓。其余的每一件,都是上了年头的,颜色褪浅,花纹淡去,然而,即便它们变成了什么模样,却还是一下子掀起了他久远的记忆。那是他们兄妹俩的玩具,兮萝当时还是刚对声音和颜色十分敏感的时候,他年纪稍长了,自诩拨浪鼓这样的幼稚东西已经入不得他的眼了。他便把自己的拨浪鼓拿来,逗兮萝玩儿,每一次,都能把她逗得咯咯直笑……还有那个小弹弓,小木马,小木剑……慕容北辰被这些刺激得心中潮绪翻滚,眼眶一点点变红,胸腔中似有无数压抑憋闷的情绪在翻滚着,叫嚣着,汹涌着。他伸手,紧握成拳,狠狠一锤,直把那桌子震得差点碎裂。正痛哭流涕的两人被他的动静惊住,转头看他。他开口,声音干涩,“她为什么不去找我们?”既然她好端端地活着,既然她知道他们兄妹两人身在何处,过着什么日子,既然她做出一副对他们念念不忘的样子,这些年,为什么不去找他们?为什么要呆在这里,拿着这些所谓的旧物,写着这些酸溜溜的信,只把她所谓的不舍和思念全都投注在这样毫无建树的枉然之中?